當我們想到亨利·大衛·梭羅時,我們會想到他在瓦爾登湖。事實上,讀者可能會想象他在那裡度過了他的整個成年生活,種植豆子和從結冰的池塘表面彈起鵝卵石。但事實上,梭羅在小屋裡呆了兩年多一點。其餘時間,他作為付費客戶住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家庭寄宿公寓。是的,他歌頌永恆。(「我認為我的腿開始移動的那一刻,我的思想開始流動,」他曾經寫道。)然而,他基本上堅持自己的洞穴,除了一個顯着的例外:一個漫長的睡衣派對,分為兩個不同的章節,在家裡他的好朋友兼導師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梭羅魚 1841 年 4 月首次加入愛默生家族。那時,愛默生正在與社區主義理想打交道,毫無疑問,在附近的烏托邦布魯克農場大院裡,房客的想法比推糞更可口。此外,愛默生還很喜歡他的年輕朋友。他認為梭羅是一個門徒、事實者、個人治療師。「我和他一起工作,因為我不應該沒有他,」愛默生告訴他的兄弟威廉,並補充說,房子的最新成員是「一位學者和詩人,像一棵年輕的蘋果樹一樣充滿希望。」

一開始,梭羅當然是這段關係中的初級合伙人。愛默生已經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和神學特立獨行者,出版了《自然》(1836 年)並放棄了他在波士頓第二教堂的講壇。梭羅是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畢業生,作為一名教師而退伍。他比他的主人年輕 14 歲,盡最大努力像愛默生一樣走路,像愛默生一樣說話——詩人詹姆斯·羅素·洛厄爾形容這種模仿的壯舉「非常有趣」。這是類固醇的英雄崇拜,帶有強烈的孝道。
還不止這些。在與他的偶像短暫旅行之前不久,梭羅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們朋友的聖地與任何上帝的聖地一樣神聖,以神聖的愛和敬畏接近。」 這種友誼是一種精神事業,一種志同道合的靈魂,雙向流動。帶來快樂並最終造成痛苦的能力也是如此。你可以說梭羅和愛默生的故事是一個愛情故事。然而,梭羅對他導師的妻子越來越依戀,這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對梭羅來說,利迪安·愛默生不太可能成為愛情對象。1841 年,她是一個 38 歲的兩個孩子的母親,對自己的婚姻有着複雜的感情——她尊敬她的丈夫,她稱他為愛默生先生,但看到他對基督教的貶低越來越痛苦。並不是說 Lidian 是一個重讀聖經的狂熱分子。她的信仰是不拘一格的,包括加爾文主義的嚴格和一神論的陽光。(她甚至在十幾歲的時候經歷了一個隱士階段,餓着自己,跳過家具作為塑造性格的練習。)然而,她對沃爾多的觀點感到困擾——「製作你自己的聖經,」他曾經寫道——並且,感覺與她微笑的天鵝頸配偶隔絕了,開始為婚姻的漫長旅程做好準備。
她也是一個可愛的神經質的人。如果在整理房子的過程中,她把一本更大的書放在一本較小的書上,她會在半夜醒來糾正這個邪惡的安排。她對每一種生物——牛、貓、雞——都有最強烈的同理心,並且寧願護送一隻蜘蛛到外面而不是殺死它。隨着歲月的流逝,她退回到憂鬱症的迷霧中,在床邊放着四五本厚厚的醫學教科書,用她丈夫的話來說,就是「罌粟和燕麥片」。毫無疑問,麗典時不時會生病。但是,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她很可能上床睡覺是對家務勞動和情感上的無聲抗議。
梭羅身材矮小、樸實、熱情、崇拜沃爾多的形象出現在這一幕中。我無法想象兩者之間有任何傳統的調情。的確,梭羅非常害羞,以至於他無法不臉紅地穿過愛默生廚房,那裡有兩個年輕的女僕。此外,還有兩個忙碌的人:麗典經營着一個熙熙攘攘的家庭,不僅要養活自己的家人,還要養活一大群愛默生的粉絲和超凡的遊客;梭羅在任何一天都會植樹、和孩子們玩耍,或者為他的導師的手套建造一個狡猾的木箱。
當然,這裡和那裡都有關於日益融洽的僵化暗示。由於未能將她的丈夫帶回一神論者的圈子,莉甸與梭羅分享了她的精神衝動。1843 年 1 月 24 日,當愛默生外出講學時,梭羅告訴他,利甸「幾乎說服我成為基督徒,但我擔心我經常陷入異教」。Lidian 本人對梭羅在教堂的出席感到驚喜,無論多麼短暫。在另一個場合,她被他收到一個八音盒作為禮物而激動得不得了,她說:「我比以前更喜歡人性。」
這些都不是浪漫的東西。然而,事情正在發生。在那段漫長的日子裡,在劍橋收費公路上的白宮裡,某種深深的感情萌芽了。奇怪的是,這種感覺的發展沒有記錄,因為梭羅和他的圈子以接近實時的方式記錄了他們的生活。在你把它寫下來之前,你幾乎沒有經歷過。但也許梭羅對《利迪安》日益增長的依戀實在是太放射性、太危險了,以至於他無法致力於紙上談兵。
不,那得等他離開愛默生家了。1843 年 5 月,他一直呆在那裡,但有一些短暫的中斷。那時,梭羅找到了一種方法來逃離他導師的引力軌道,同時仍然與家人保持聯繫:他搬到史坦頓島與愛默生的兄弟威廉一起住。在那裡,他會輔導威廉的兒子,在曼哈頓密集的城市人口中驚恐地退縮——而且,顯然,他對利甸充滿了渴望。5 月 22 日,他到達後不久,給她寫了一封信:
我相信和你的很多對話都沒有完成,現在我確實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但我會恢復一些未完成的沉默。我會毫不猶豫地認識你。我認為你是我的一個姐姐,我無法避免——一種月球的影響——只有像月亮這樣的年齡,它的時間是由她的光來衡量的。
這封信以這種方式持續了一段時間。至少可以說,這是非常崇高的——反映了梭羅對利甸的強烈感情,也是一種迴避的策略,一種對線索的思考,因為這些感情被定義為禁止的。如果她是他的妹妹,她當然不可能成為性慾的對象。這對月亮來說翻了一番,在這種情況下,它的處女光很好地消毒。這封信繼續引用梭羅最可愛的肯定之一,在大流行封鎖期間尤其令人振奮:「沒有什麼比擁有遠方的朋友更能讓地球顯得如此寬敞了。他們製作緯度和經度。」 然後它冷卻到一個更溫暖的溫度,向孩子們和愛默生的老母親致以問候,「今年夏天我應該很高興在這裡看到她康科德的臉。
也許,你說,這是一個孤獨的人孤立地爆發。或許,這也只是一個例子,說明當時很常見的友誼詞彙,現在不太常見。但是這封信之後又是另一封,在 6 月 20 日,在 Lidian 給他回信之後。(她的回覆丟失了。)梭羅告訴他的記者,他在日落時分到山頂去讀她寫的東西。這句話對他來說是活生生的,幾乎聽得見:「你的聲音似乎不是聲音,而是來自藍天,就像來自紙張一樣。」 然後他轉向另一個天體比喻:
一想到你,我的生活就會不斷地升華,那將是永遠在地平線上看的東西,就像我仰望晚星一樣。我想我不用見你就知道你的想法,在康科德也是如此。你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
這是愛嗎?它沒有任何形式的色情熱,這並不奇怪。梭羅在談到自然世界時是一個感官主義者,他似乎將自己的身體視為未知領域。「我必須承認,沒有什麼比我自己的身體更奇怪了,」他在去年的日記中透露。「我愛任何其他的大自然,幾乎,更好。」 誠然,他剛剛失去了他心愛的兄弟,在他自己出現了同樣疾病的(心身)症狀之前。他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的血肉之軀。
但讓他反感的是陌生感。在愛默生的肘部,他構想了一個宇宙,其中所有事物都相互關聯——除了他自己,而且頻率令人沮喪。「我們的生活必須多麼孤獨!」 他在日記中哀嘆道。「我們住在海邊,我們和大海之間沒有任何東西。」 多年來,莉迪亞一直試圖闖入她丈夫孤獨地密封隔間,不知何故,她進入了梭羅的房間。她對他一點都不陌生。
在這一點上,許多梭羅主義者會大喊犯規。如今,我們了解到梭羅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同性戀者,他回到他在瓦爾登湖風化的小屋裡不僅是對新英格蘭膽怯的打擊,而且是反異性戀的抨擊。達成這個共識花了一點時間。沃爾特·哈丁是他偉大的現代傳記作者之一,最初因在「亨利·梭羅的日子」(1965)中輕描淡寫的主題而受到批評。作為一種懺悔,哈丁對梭羅的作品進行了第二次法醫掃描,這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並在 1991 年的《同性戀雜誌》上或多或少地將梭羅任命為同性戀者。到目前為止,有一整部文學作品都致力於描述梭羅作為酷兒化身的角色。那麼他和立電的關係又會如何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我們找到它的地方。不是因為我相信梭羅與麗典有任何性關係。似乎沒有人相信這一點,除了小說家艾米·貝爾丁·布朗(Amy Belding Brown)之外,她在「愛默生先生的妻子」(2005)中想象了在乾草棚里的一次半可信的幽會。錯誤是將梭羅與麗典的關係視為一種空殼遊戲,在任何數量的隱瞞下都潛伏着一種普通的異性戀戀情。相反,我會爭辯說,這是他對男人和女人、愛和性的巨大困惑的完美典範。
並不是說他從來沒有就這些話題發表過言論。梭羅寫了兩篇散文,「愛情」和「貞潔與性感」,理論上應該為我們清除空氣。然而,它們主要是脆弱的東西。在第一篇文章中,梭羅訴諸超驗主義解碼器環,將每一種形式的善良轉化為另一種形式:「情人在他心愛的人的目光中看到的美麗與日落時描繪西方天空的美麗相同。」 他還建議,破壞這種情緒的最快方法是泄露它們。
第二篇文章更具有啟發性。梭羅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放蕩者,他認為應該更坦率地討論性問題,而謹慎者則明顯鬆了一口氣。有一些關於節制是美德的胡言亂語,欲望被梭羅所謂的「更高尚的快樂」——純潔、勇敢、英雄主義——排擠。他也是為了童貞。但隨後他對植物王國表示了認可,它的「生殖器官」「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換句話說,我們都應該像無恥的花朵一樣,將我們的濫交戴在袖子或花蕊上。這是一個令人驚訝和熱鬧的逆轉,接下來是兩篇文章中最誠實的一段:
我夢到過的兩性交配,美得令人難以置信,美得讓人難以忘懷。我曾有過這樣的想法,但它們是我經歷中最短暫、最無法挽回的。奇怪的是,人們會說奇蹟、啟示、靈感之類的東西已經過去了,而愛卻依然存在。
對梭羅來說,性只不過是一個謠言,一個迅速消散的夢想。愛是另一回事:最後的奇蹟。他不知道該怎麼做,因為他被女性和(主要是)男性吸引,渴望分享他的感受,並完全相信這種披露會永遠殺死他們。
正如我所提到的,還有第二章。1847 年 9 月,梭羅從瓦爾登湖的荒野回歸文明——也就是說,回到愛默生的家。這種轉變具有一定的諷刺意味。在池塘邊,他已經住在愛默生的土地上,他的朋友幾年前購買了這塊土地,並宣稱自己是「14 英畝的地主和水主」。
但他的居住條件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權力的平衡在梭羅和他的上師之間發生了變化。到 1847 年,他已經撰寫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馬克河上的一周》一書的草稿,並為《瓦爾登湖》收集了大量原材料。。」 他不再是一個搭檔——事實上,他對大規模敘事的掌握現在超過了他的導師。與此同時,兩人之間的友誼一直在破裂。早在 1843 年,愛默生就抱怨梭羅的散文,不斷地爭論悖論,使他「緊張而悲慘」。他認為他的前門生逃避人頭稅,以及隨後在監獄中度過的那一晚,都是「偷偷摸摸,品味低劣」。梭羅也同樣黃疸,抱怨愛默生特有的超脫:「我的朋友身體在場時,我從來沒有像他不在時那麼親近。」
另一個很大的不同是,在梭羅第二次逗留大約八個月期間,愛默生在英國進行巡迴演講。他願意讓年輕人擔任他的家庭代理人,這表明兩人之間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信任。但這也意味着角色發生了變化:如果梭羅和利迪安第一次演年輕戀人,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了夫妻。梭羅在 11 月 14 日的一封信中告訴愛默生:「我和麗典是非常好的管家。」 (「她是我非常親愛的姐姐,」他很快補充道,以免他的通訊員誤會。)梭羅還特別喜歡愛默生的孩子們,他們崇拜他們的家庭教師。事實上,在上面引用的同一封信中,他似乎在刺激他的老闆贊助人。年輕的愛德華·愛默生,他注意到,問他,「先生。梭羅,你願意做我的父親嗎?」
在艾默生缺席的大部分時間裡,Lidian 都躺在床上。他長期退出家庭生活使她沮喪,他對她的信件的冷淡而正確的答覆也使她沮喪。她的脆弱可能加劇了她與梭羅的關係。畢竟,他們都被同一個男人所奴役,而且彼此之間是一種特殊而令人惱火的三角戀。同樣,我們無法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這裡有一種有趣的空虛,這是梭羅早先所說的「未完成的沉默」的另一部分。他對麗典的感情消失了嗎?
我想不是。1848 年,很可能是在愛默生回來並且梭羅永遠離開這個家庭之後,梭羅再次向利迪安致辭,這一次是在他的日記中。他沒有使用她的名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早期從史坦頓島發出的信件的連續性。「我仍然認為你是我的妹妹,」他寫道。「我想認識你。其他人是我的血緣親屬或我的熟人,但你是我的。」 他補充說:「我不知道我從哪裡開始,你從哪裡開始。」
這不僅僅是愛的宣言,而是一種欣喜若狂的融合,或者至少是對一個的渴望。梭羅長篇大論,創作了一些美麗的東西,也許與手頭的主題一樣陶醉於那種美麗。「當我愛你時,我感覺好像我在吞併另一個世界,」他宣稱。「我們拼接天堂。」 他以一個狂野的綽號作為結尾,其修辭符合聖經,人們想象的另一方面,他始終如一的孤獨和陌生感:
我的精神在思想中不斷擁抱誰。我流向誰誰與我不分離。誰一身白衣誰來如香。誰是我能想象到的一切——我的啟發者。我的女人味。
在這裡引起我注意的是最後一句話,它奇妙地混淆了男性和女性可以互換的感覺,而且可能除此之外。在我們為它命名之前,它是性別流動性,以及浪漫套牌的重新洗牌。說到這裡,梭羅可能永遠不會再和利迪安談起他的感受,除非在 1848 年他們停止玩房子之後。酷兒(在他這個詞的意義上,也許在我們的意義上)。「我害怕屍體,」他曾經寫道,「我害怕見到它們。」 但靈魂是另外一回事,他肯定覺得李典窺視了他的,他也窺視了她的。那是天上的拼接手術,這可能是這位偉大的孤獨者對愛情最好的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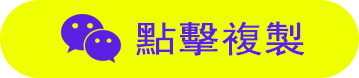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聽別人說過,值得推薦的情感機構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