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的暢銷書《黑箱》《82年生的金智英》開始,女性議題成為文學的一面側重。而紀錄片《人間世》、日劇《坡道上的家》的上映,也讓人們把目光投向母親這一層女性身份,並試圖衝破一貫的溫馨場景和蒼白無力的歌頌,從真實到幾乎有些殘酷的視角,直述她們的弱勢、困境、痛苦。
今年《坡道上的家》國內譯本出版,再次把家庭主婦里沙子和安藤水穗的故事放在我們面前。初為人母而手忙腳亂、精神恍惚的水穗失手溺死了自己的女兒凜,無論如何,慘案發生,她將為此面對嚴厲的法律制裁,而和她有着類似為母經歷的里沙子,是這場特殊審判的陪審員之一。
本篇選自其中第一章,部分內容有刪減。
里沙子今早七點出的門。五點半起床,她先打理好自己,接着做早餐給女兒文香吃,再叫醒丈夫陽一郎。隨後將文香託付給住在浦和的公婆,隨即前往霞關。

作為一名候補陪審員,今天是她去參加法庭現場的第一天。
這是一起虐嬰致死案。東京市內,一名三十幾歲的女性,將八個月大的女兒扔進了放滿水的浴缸。丈夫回家發現後,趕緊將女兒送去醫院,但還是沒能挽回女兒的生命。這位女性供稱:「因為女兒哭鬧不停,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不得已才把她扔進了浴缸。」因此,警方認定這起案件是故意行兇,並非意外,於是以涉嫌殺人罪逮捕了那名女性。
雖說類似的虐童新聞幾乎每天都有,一不小心就會搞混淆,但里沙子的確記得在報紙上看到過這起案件。她清楚地記得,讀到「把女兒扔進浴缸里」時,自己皺起了眉。
影版《坡道上的家》中的里沙子
在工作人員的引領下,她和其它陪審員、候補陪審員一起,列隊走進法庭。全體起立,審判開始。法官要求被告人往前站。
里沙子直瞅着站在面前低着頭的女子。她穿着白襯衫搭配灰色長褲,一頭微卷長發掩住了她的臉。法官詢問她的名字與出生年月日時,她總算抬起頭。
「安藤水穗,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生,無業,住在……」
是位皮膚白皙、長相端正的女子。細長的雙眼、直挺的鼻樑、薄薄的嘴唇,要是化了妝的話,肯定更好看吧。里沙子這麼想着,從女子身上移開了視線。
影版《坡道上的家》中的安藤水穗
認識她的人都無法相信她會做這種事。鄰居接受電視台採訪時也是這麼表示的。「她人很好啊!怎麼可能做出那種事?」「她很有禮貌,見到人都會打招呼……」
里沙子現在也是這麼想,因為面前這位叫安藤水穗的女子看起來和一般人無異,或許正因為如此,里沙子才感到恐懼,以至於無法一直看着她。
她真的就是一般人。
如果自己在周遭淨是素昧平生之人的場合下,遇到這位名叫安藤水穗的女子,里沙子也許會主動向她搭訕,因為兩人年紀相仿,她長得又秀麗。
不過,正因為她看起來很普通,才讓這起案件在里沙子心中多了許多真實的色彩。案發當時,這位名叫安藤水穗的陌生女子雙手抱着嬰兒,那股溫熱感、柔軟感,像切身記憶般在里沙子的雙手間擴散開來。她的耳畔仿佛迴蕩着嬰兒的哭聲,那肆意的、永遠也不會停止似的哭聲。浴室的濕氣與味道,甚至連腳底踏在毛巾上的觸感都能感受得到,就像自己正抱着一個哭個不停的嬰兒,站在那裡。
接着,雙手突然感受不到嬰兒的重量了,眼前只剩十指張開的雙手。
對於審判一事,里沙子可以說是門外漢。雖然聽過簡單說明,也讀過相關書籍,卻還是沒什麼概念,她只好集中精神,聽着審判長說話。坐在水穗對面的檢察官——那模樣讓人想起連續劇里常會出現的女強人——滔滔不絕地說着話。
女檢察官一邊陳述,一邊反覆強調水穗是蓄意殺人。
水穗的女兒凜生於二○○八年十二月。雖然夫妻倆開開心心地迎接新生命的到來,但水穗表示,回家後,凜連續好幾天都吵鬧着不睡覺。被女兒折騰得痛苦不堪的她甚至抱怨自己根本不想生小孩,這是把凜接回家後不到一個月的事。
丈夫也盡力幫忙照顧孩子,但慘劇發生之前,剛好他忙着準備資格考試、加班等,常常很晚才回家。儘管這都是水穗生產前就發生的事,但她總是埋怨丈夫不幫忙,怨嘆自己的人生被逼得亂七八糟。
由於水穗和原生家庭相處不睦,丈夫只好向自己的母親求援。婆婆來幫忙帶過好幾次孩子,但水穗頻頻以「她嫌我抱小孩的姿勢不對」「再這樣下去就要被那個人吃得死死的了」為由,拒絕婆婆幫忙。
凜逐漸長大,卻總是不肯乖乖睡覺,哭鬧不停,怎麼吃都還是瘦巴巴的。種種育兒挫折讓水穗失去了自信,也就對女兒萌生恨意,總想着要是沒有生她的話,自己就可以過上想要的人生了。
丈夫回家後不是看到女兒躺在臥室的床上哭鬧,妻子卻坐在客廳看電視,就是女兒晚上哭泣,水穗卻一副想逃離似的樣子躲到別的房間。
凜六個月大時,丈夫發現女兒的腳和屁股上有掐、打之類的傷痕。水穗在丈夫的質問下,坦白自己曾經對孩子施虐,也保證不會再犯,但那之後女兒身上還是頻頻出現抓痕、紅腫之類的傷。
擔心不已的丈夫向朋友傾訴煩惱,也聽從友人的建議申請了保健師上門訪問,訪問日就訂在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慘案發生的兩天後。
水穗以「嬰兒比想象中更難照顧」這樣幼稚又自私的理由,放棄為人母的責任。而且一想到女兒越長大就會越有主見,也就越不受控,她對凜的恨意更深了。再者,她很害怕別人察覺自己厭煩照顧孩子一事,所以強烈排斥婆婆和其他人的介入與援助。
從慘案發生後水穗和丈夫的對話,以及案件發生前,她一如平常地做家務,還和朋友通過電話來看,她不是沒有能力判斷自己做了什麼事,也不是缺乏自控力,沒辦法克制自己的衝動。
身穿西裝的女士利落地念着這篇偶爾蹦出幾個生僻字的文章。與此同時,里沙子在腦中整理要點,在資料一角記下了筆記。她倒不是想積極參與審判,只是想站在自己的立場理解這起案件。
里沙子聽着檢察官鏗鏘有力的陳述,不由得想起一些事。
當年自己的女兒文香出生,那一刻,丈夫陽一郎感動得大哭。里沙子看到他的樣子,頓時有種自己總算完成了一項艱巨任務的心情,也激動得哭了。一旁的護士和醫生怔怔地看着號啕大哭的夫妻倆。
產後第五天,里沙子帶着標準體重的文香出院,回到了當時住的地方。陽一郎叫出租車送她們回家後,便趕回公司處理事情。
和一個幾天前還根本不存在的小傢伙獨自待在熟悉的家,那種奇妙的感覺里沙子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
她當然已經有心理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到來,雖然準備工作稱不上完美,但細節都注意到了,嬰兒床、襁褓、玩具、奶嘴、奶瓶和嬰兒車等一應俱全。但她還是覺得很奇妙,畢竟一個星期前離開這裡時,這個孩子還沒出現在這世上。而現在孩子就在這裡,充滿新鮮感地看着身邊那些早已融入她生活的東西。哎呀,她應該能看見那些東西吧?要是眼睛看不見,可就麻煩了。
想到這裡,里沙子就覺得眼前朦朧映着的室內光景,那電視屏幕、餐桌、裝飾在柜子上的照片,在自己眼中仿佛也成了一番新鮮的光景,而且那種新鮮感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乖乖躺在嬰兒床上的寶寶突然哭了,纖細微弱的哭聲緊揪着里沙子的心。她趕緊抱起嬰兒,好好安撫。本以為這下應該不哭了,沒想到嬰兒的臉卻越來越扭曲,哭到臉逐漸漲紅。
里沙子趕緊袒胸,讓嬰兒含着乳頭,無奈她還是哭個不停,里沙子只好讓嬰兒躺在地板上,確認是否要換尿布,結果尿布沒濕,也沒有便便。里沙子又抱起文香,一邊「怎麼辦,怎麼辦」地喃喃自語,一邊安撫她。顫抖的聲音,讓里沙子發現自己正恐懼不已。
怎麼會這樣?里沙子極力否定這種情緒。為什麼要覺得害怕呢?期待已久的小生命終於來到了這個家,怎麼會覺得害怕呢?未免也太奇怪了。
她這麼告訴自己,試圖穩定心緒,可這股恐懼感卻越來越強烈。在醫院結識的其他太太應該都回家了。大家一定都自然地扮演起了母親這個角色,可以得心應手地安撫嬰兒,讓小寶貝不再哭泣吧。
「真是不可思議呢!」比里沙子早三天生下孩子、準備出院的宮地太太就曾神情恍惚地說,「明明一直擔心自己連孩子都抱不好,結果一下子就抱得很順手。看來我們的體內都潛藏着母性本能,孩子一出生,那本能就發揮效用了。」
「是嗎?那我就放心了。」另一位剛順利生下早產兒、孩子正待在新生兒室的母親也說,「一定也可以擠出很多乳汁的,因為我們有母性本能嘛,所以一定沒問題的。」
里沙子想起這些話。在她忙着哄孩子的這段時間裡,太陽不知不覺西沉了。孩子卻哭得越來越厲害。屋內的餐具櫃、電視、陽一郎脫掉的襪子和隨手攤放的報紙,都閃耀着金色輪廓。好可怕,好想逃出去,好可怕。里沙子邊聽着拼命往耳朵里鑽的哭聲,邊這麼想。
過了一會兒,孩子像是哭累了,睡了過去。里沙子將睡着的孩子放在嬰兒床上端詳起來,那如同花瓣的小嘴微張;窺看她的耳朵,明明身體還這麼嬌小,精巧的皺褶就已經延伸到了耳朵的最深處;打開她輕握的手,已經有了清晰的掌紋;不但會長牙,指甲也會變長。
想到這些,里沙子害怕的心情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內心總算湧起了收穫小生命的喜悅。屋內開始變暗,但要是開燈,怕會吵醒孩子,所以里沙子沒有開燈,她用手指輕撫文香的額頭,小嬰兒蓬鬆的頭髮異常柔軟。「你是我的孩子,謝謝你來到我們家。」
總算感受到了,這就是宮地太太說的那種心情嗎?太好了。看來自己體內也有着母性本能。
出院那天的奇妙心情,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鮮感、恐懼感瞬間消失,里沙子隨即開始了忙碌的育兒生活。
晚上總是被嬰兒的抽泣聲吵醒,明明躺在嬰兒床里的文香正哭泣着,睡在同一間房的陽一郎卻還能睡得很熟。里沙子餵文香吃奶,文香卻還是哭個不停,心想明天還要上班的老公要是被吵醒也挺可憐的,於是里沙子走出房間,在昏暗的客廳安撫孩子。好不容易哄好了,可一放回嬰兒床她就又開始哭泣。嬰兒的工作就是哭,里沙子如此安慰自己,又抱起孩子。結果這樣搞得里沙子睡眠不足,身心疲累至極,她不由得懷疑:這孩子是故意欺負我嗎?文香會不會在想「我絕不讓你這傢伙好好睡」呢?里沙子認真地懷疑起來。
但一早起來,她又為自己的胡思亂想感到可笑,因為嬰兒雙眼清澄,怎麼看都不可能有這種壞心眼。
終日睡眠不足加上疲勞過度,里沙子頻頻出現類似貧血的症狀,於是趁文香滿月體檢時,自己也順便問診。醫生建議別讓孩子睡嬰兒床,讓她躺在母親身邊一起睡。果然,文香半夜哭鬧的頻率減少了許多,但里沙子只要稍微翻身,文香就會醒來哭個不停。里沙子只好側躺,像讓文香聽心跳一樣摟着她,但不能隨意翻身的後果,就是里沙子根本無法熟睡。
收起回憶,里沙子看着低頭坐在法庭里的安藤水穗,頭髮遮住她的臉,看不見她的表情。「你一定也很辛苦吧。」里沙子心想,「其實稍微忍耐一下就能撐過去了啊!嬰兒階段一眨眼的工夫就過去了,難道你的體內沒有母性本能嗎?」
接着是律師的陳述。坐在水穗身後,頭髮花白的男士起身面向大家。他看着陪審員們,指手畫腳地開始講述。雖然這在里沙子看來有幾分刻意,但他的陳述十分容易理解。
二○○四年秋天,水穗經由朋友介紹,結識了丈夫壽士。翌年初春,兩人打算結婚。六月登記,小兩口便開始了新婚生活。那時,水穗任職於進口食品公司,壽士則是在運動用品店工作。
婚後還不到一年,兩人的關係便出現了裂痕,起因是比起家庭,壽士更看重自己的興趣與朋友。每次水穗想要和他談談,壽士便一副火冒三丈的樣子,大聲咆哮。雖說兩人交往時間不長,但印象中,壽士是個性格沉穩、脾氣很好的人,所以水穗十分詫異丈夫婚後的改變,驚懼不已。
婚後第二年,水穗一直沒有懷上孩子,婆婆開始擔心媳婦的身體有問題。於是水穗在丈夫的陪同下,一起去婦產科做了檢查。當醫生說其實夫妻倆的身體狀況都很正常時,水穗心想,或許有了孩子,就能夠改變壽士的生活作息,改善夫妻關係,於是主動向丈夫提出想要孩子的心意。壽士說,如果水穗想在孩子長大前辭去工作,專心育兒、操持家務,自己就要換個收入較高的工作。至此,兩個人對要孩子的態度都變得積極起來。他們接受專業諮詢,看了三次門診後,水穗順利懷孕,於二○○八年十二月生下女兒凜。
可水穗沒想到自己的期望落空了。她和剛出生的孩子出院回家後,丈夫還是經常不在家,理由是被孩子整夜整夜的哭聲吵得無法入眠,影響工作。壽士倒也沒有完全不照顧女兒,卻也僅止於心血來潮,所以實在沒幫上什麼忙。再者,水穗很怕丈夫大發雷霆,不但不敢提出任何意見,也不敢向丈夫傾訴煩惱。
至於水穗為什麼沒有向丈夫以外的人求助,而是全都悶在了心裡,也有她的理由。
不論婆婆,還是體檢時的保健師,都和水穗說,她的女兒在情感表達方面似乎不如同齡孩子那麼豐富,有些發育遲緩。這些無心的批評讓水穗深感迷惘,她也變得對別人的意見感到不安,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不如其他母親。因此,她不敢向相關政府單位、專業保姆等諮詢,怕只會換來更多批評,久而久之就放棄尋求外援了。
在只有嬰兒相伴的孤獨日子中,感覺自己被逼至絕境的她曾向學生時代的幾位朋友求助;雖然有育兒經驗的朋友曾去她家拜訪,聽她訴苦,並給予了一些建議,卻還是無法減輕水穗內心的重擔。
就算孩子哭個不停,也沒有抱起來哄慰的力氣。水穗向好友坦白自己沒有自信能照顧好孩子,好友覺得她可能患上了產後抑鬱症,建議她去看心理醫生。
六月時,水穗去了自家附近的診所,掛號時她想到,丈夫要是知道了這件事肯定會暴怒,於是,擔心被臭罵的她臨陣退縮,打道回府了。
此外,案件發生約一個月前,水穗通過丈夫的手機發現他和前女友又開始往來了。萬一壽士要求離婚,只剩自己和女兒相依為命,又該如何是好呢?水穗想到這些,更加憂心了。
水穗不太記得案發當天的情形,只記得壽士發來信息,說馬上到家。
水穗心想,得趕在丈夫回來之前幫女兒洗好澡才行,所以去了浴室。但當時是在重新放洗澡水,還是在加熱,現在她已經想不起來了。接着凜又開始哭鬧不停,害怕惹惱壽士的水穗只能一邊哄女兒,一邊察看洗澡水準備好了沒有。再之後的情形她就完全不記得了。一回神,她才發現壽士正用力搖着自己,耳邊響着丈夫怒罵自己想要殺害女兒的吼叫聲。
被育兒的疲累逼得喘不過氣的水穗並沒有殺害女兒的意思,她只是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在抱着女兒的手鬆開時,她無法控制自己。
律師表示,檢方之所以沒有掌握這段細節,是因為在案件調查階段,水穗覺得不管說什麼都無法改變自己殺了孩子的事實,所以沒力氣為自己辯駁,她只是在取證官的有意引導下被動地回答問題,給出了並不是出於自我意志的供述。
在資料上記筆記的里沙子抬起頭,看向水穗。她依舊低着頭,頭髮遮住了臉,看不見表情。
里沙子沒想到控辯雙方的意見竟有如此差異。剛才女檢察官那番陳述將水穗說得像是惡女,現在聽到的律師說明卻又讓人覺得她是個可憐又柔弱的母親,就算她丈夫成了被告也不奇怪。
問題是,會有這種事嗎?里沙子不停地思索。僅僅是丈夫不夠體貼,醫護人員又說了讓她深感不安的話,就能讓水穗受傷到這種地步,導致她拒絕任何人的幫助嗎?想到這裡,里沙子差點「啊」地叫出聲來。倘若這裡不是法庭的話,她恐怕真的會叫出來吧。
好幾個聲音重疊着在她的記憶中浮現。
「只要讓寶寶吸一下乳汁就出來啦,很簡單的。」「你該不會偷吃了巧克力吧?」「不能因為怕痛就偷懶不按摩哦!」
為什麼忘了呢?怎麼會忘了呢?
從法院回家的路上,里沙子回想着這些事。一旦憶起,忘記的事就會像串珠般接連不斷地蹦出來。
生產前,里沙子參加了社區里開設的「媽媽教室」——實際上是「准媽媽教室」。不論是那裡,還是後來負責接生的醫院,都鼓勵母乳哺育。聽說喝母乳長大的嬰幼兒更不容易有哮喘之類的毛病,而且母乳可以促進孩子腦部發育。對母親來說,也會因為哺乳而降低罹患乳腺癌、子宮癌的概率。醫院也提出了一些精神層面的觀點,總之,哺乳可以讓母子之間的聯繫更深,母親可以感受到身為人母的喜悅,而且孩子就算長大後,也會清楚地記得被母親抱在懷裡、吸吮母乳的感覺。
生產之前,里沙子對這些事都沒什麼特別的想法,只是想:「噢,原來如此啊,既然這樣,那就給寶寶喝母乳吧。」
於是,里沙子一聽說有促進乳汁分泌的飲食方法,就會乖乖嘗試;聽說生奶油和巧克力有礙乳汁分泌,不論多想吃也會忍住口腹之慾;聽聞坐月子時不能着涼,就讓自己穿得像冬天的登山者一樣厚重,還在身上貼了好幾個暖寶寶貼;聽說花草茶對身體好,也趕快買了回來,喝到噁心為止。只要一預約上,里沙子就會跑到生產時的那家醫院複查乳房,也忍痛按摩胸部,還大老遠地跑去逗子市參加哺乳育兒講座。
「母乳能促進孩子的腦部發育。」第一次在「媽媽教室」聽到這句話時並不覺得可怕。但後來里沙子好幾次想起這句話,竟深感恐懼。
要是孩子因為自己成了笨蛋,那怎麼辦?要是因為我的問題,孩子不會念書、功課很差,怎麼辦?要是因為我……
「其實配方奶也不差。」身邊從沒有人這麼說過。但婆婆或是「媽媽教室」的講師說過:「只要讓寶寶吸一下乳汁就出來啦,很簡單的,母親的身體就是這種構造。」
「不能因為怕痛就偷懶不按摩哦!」說這話的是保健師,還是護士來着?
「你該不會偷吃了巧克力吧?」這句話我記得,是老公說的。明知這句是玩笑話,那時還是氣得想要離婚。
自己的記憶竟然如此模糊,里沙子雖然覺得驚訝,卻也能理解。因為那段日子忙碌到腦海里的記憶都斑駁了。除了為哺乳煩心之外,還要成天擔心孩子會不會一不小心從沙發上摔下來,還曾被孩子上吐下瀉的情形嚇得六神無主,不然就是孩子高燒不退,只好深夜直奔醫院掛急診。
雖然陽一郎多少會幫忙,但他白天上班不在家,又常晚歸,里沙子難免覺得沮喪、絕望,感覺自己孤立無援。
里沙子想起同樣生了孩子的朋友們。其中一位比她早一步生下孩子的朋友說過:「我們家這個特別好養。人家不是說孩子出生後好幾個月,母親都得每隔兩三個小時起來餵奶嗎?可我們家這個不但晚上很少醒,白天也不怎麼哭呢!」
里沙子總覺得對方該不會是在暗諷「你們家孩子很奇怪」吧?若非如此,實在不明白這種事有什麼好驕傲的。
離開法院去婆婆家接文香時,已經四點多了,真是漫長的一天。
「什麼?!被選上了!」婆婆這聲喊叫讓里沙子猛然回神,意識到自己該回家了。此刻,她已經累到快昏倒了。
「不過,是候補陪審員。」里沙子趕緊解釋。
「候補陪審員?」
「不是正式陪審員。只有正式陪審員突然因病缺席之類的情況發生時,才需要替補上去履行陪審員的職責。就和『替補選手』一樣。」里沙子解釋道。「不過就算正式陪審員無人缺席,候補陪審員也得每天到庭,聆聽審理經過。」里沙子又補充說。
里沙子並不想和婆婆討論這起案件。想要撒謊,卻又不知道這世上究竟都發生着什麼案件。
和公公婆婆聊了將近二十分鐘後,里沙子帶着文香再次回到浦和車站,已經晚上七點多了。
路上時,文香還吵鬧得很歡,結果回家一上床就睡着了。里沙子本來想幫她洗澡,但想想還是先弄晚餐好了。於是連衣服也沒換,洗了手便走進廚房。
飯起鍋時,陽一郎剛好回來。
「你回來啦!」里沙子邊朝走廊那頭喊,邊擺餐具。
「沒想到你還真的被選上了!」
「我到現在還是眼前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是形容腦子的吧,眼前應該是一片黑暗。」
「一樣啦!眼前是白的, 腦子是黑的, 反正都是形容心情很絕望。」
「你又不懂什麼法律,能聽懂他們在說什麼嗎?」
「聽得懂啊。我聽法官說,原本法庭上講的都是專業術語,但自從採用陪審員制度後,就都改用淺顯易懂的話說明了。」
里沙子突然噤口,開始猶豫。她一方面想和陽一郎聊聊這起案件,一方面又有些牴觸。為什麼會牴觸呢?里沙子自己也不明白。是因為自己都還沒釐清思路嗎?還是擔心這個話題會讓人心裡不舒服呢?但她終究無法保持沉默。
「那個案子啊,是關於虐童的。」里沙子說,「你還記得嗎?這個案件去年還上過報紙呢。說是有個三十多歲的家庭主婦,把孩子扔進浴缸里淹死了。」
「咦?沒印象啊,每天都有虐童新聞,昨天又有一起啊!好像是小孩被母親的情人給打了什麼的。」
餐桌上霎時一片寂靜。
里沙子想要回憶起今天的事,內心深處卻很排斥。起訴書上那些被逐一念出的字句仿佛全都崩解、消失,變得模糊了,唯獨罪行、殺人等字眼牢牢地黏附在耳朵里。
「我真的不懂審判, 可是檢察官和律師, 他們講的完全不一樣啊。這方說A,那方說B,到底是哪一方說謊呢?」明知陽一郎會對這種幼稚的疑惑很無語,里沙子卻很想知道答案。
「這不就是你們接下來要查清楚的嗎?」陽一郎隨口回應着,用筷子夾了一塊可樂餅。
周圍安靜得只能聽到陽一郎的咀嚼聲。兩人同時沉默,里沙子莫名地覺得氣氛有些緊張。
「對不起。」里沙子道歉。
「怎麼了?」
「其實你不想聽這種事吧。」
「倒也不是不想聊這件案子,我明白你第一次碰到這種事,難免會有很多不安,所以沒什麼好道歉的。」
無論是檢察官還是律師的陳述都讓里沙子聽得很痛苦,也時常恍神漏聽。里沙子並不想看向水穗,可又沒法不在意她。每當看向她時,她總是正面無表情地看着地面。里沙子很想把這些瑣碎的記憶全都和陽一郎分享,但還是沒能說出口。
「我是如何看待安藤水穗這個女人的呢?」夜裡,趁陽一郎陪文香睡覺,里沙子邊泡澡邊獨自思索着。就算不願想起來,腦中還是會浮現她那張沒有化妝的臉。
水穗始終低着頭,所以看不見她的表情。法官念完起訴書之後,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她悄聲回答沒有。或許是認識到了自己犯下的錯,覺得不可能無罪脫身吧。還是因為……
泡在浴缸里的里沙子站起來,低頭看着搖晃的水。
安藤水穗也是像這樣在浴缸里放滿了水嗎?為了溺死孩子……她是專門為了溺死孩子而放的水呢,還是用了前一天用過的洗澡水呢?
明明這種事根本無關緊要,里沙子卻無法停止思索。孩子是被扔進了乾淨的水裡,還是前一天泡過的混濁洗澡水裡呢?
里沙子感覺內心的恐懼被喚醒了,趕緊走出浴缸。分不清從額頭淌下的是水滴還是汗;她將水溫調低,沖了一下澡,離開了浴室。
瞧了一眼臥室,陽一郎和文香都睡着了。面對面地睡着的父女倆,連蜷縮的睡姿都很像,擱在兩人中間的毛毯捲成一坨。
里沙子關掉浴室和廚房的燈,設定好六點的鬧鐘,幫文香重新蓋好毛巾被後,躺在她旁邊。一閉上眼,腦海中便浮現出今天看到的各種景象。
睡不着,想着要不要開個空調,又怕習慣踢被子的文香會感冒。
不,睡不着不是因為悶熱。
里沙子躡手躡腳地起身,走出臥室,經過昏暗的走廊走向廚房,打開冰箱拿了一罐啤酒。
「要是不快點睡覺,明天開庭時搞不好會睡着。坐在那裡打瞌睡的糗樣,從旁聽席可是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趕快喝個精光,早點入睡吧。」
里沙子站在昏暗的廚房裡喝着啤酒,冰涼的感覺讓她心情舒暢。
明明不想胡思亂想,結果一回神,里沙子又想起文香八個月大時的事,仿佛昨天才發生似的,其實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那時,常有不認識的人誇讚文香是個粉嫩可愛的小女孩。對了,那時一直還不會坐的她,突然學會坐了。里沙子想起,看到女兒像大人一般坐着時自己不由得笑了。那時的文香就像個跟屁蟲,緊黏着里沙子。陽一郎不在時,里沙子連上洗手間都不敢關門,因為文香看不到她就會大哭……
如此柔軟、嬌小,還不會走路,有着清澄雙眼的生物——竟然將這樣的孩子——不行,今天不能再多想了。
里沙子大口喝光剩下的啤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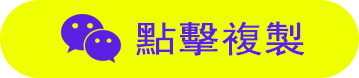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朋友諮詢過,還真的挽回了愛情,現在兩人已經結婚了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
求助
可以幫助複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