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動與世界斷聯的這一年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少熬點夜吧,熬夜傷肝時間長了不好。」
「都熬習慣了啊哈哈哈,你咋這麼養生?」
配圖 | 《中國醫生》劇照
1
2020年的夏天是我與這個世界斷聯的開始,當時我考研失敗,就快要拿到大學畢業證書,正在一家電商公司實習,每天早上趕7點半的那趟公交,抱着沉甸甸的保溫餐盒坐在公車座位上搖搖晃晃,從東邊城鄉結合部的窄巷子裡一路繞到城北。下車就要飛奔,直到手機接收到寫字樓上班打卡的信號,才能長舒一口氣隨着人流慢慢擠進電梯。
我的實習工作主要是負責產品平台宣傳,每天跟着組長研究受眾喜好,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後漸入佳境,只等着拿到畢業證書轉正入職,開啟社畜萌新生活。
但沒想到,期待中的新生活,竟然是人生一場噩夢的開始。
我從小身體健康,雖然是個運動廢柴,但抵抗力還算優秀,即便在流感肆虐的冬天也能在大學宿舍里全身而退,從來沒有住過院。
起初只是喉嚨疼,當時我還在專心考研,每天對着成堆的備考資料,以為只是壓力太大導致的上火,便沒放在心上。
症狀持續了半年都沒有緩解,甚至說話發聲都變得異常困難,有時半夜還會被喉嚨里的劇痛疼醒。8月我去醫院做了喉鏡,醫生說我聲帶下長了「新生物」,讓我吃藥看看情況。我邊實習邊吃藥,最後徹底說不了話了。我每天冷汗從後背透到前胸,開始用本子和筆與別人交流,不斷適應着成為「啞巴」的自己。
9月我換了一家醫院看專家門診,醫生戴着巨大的口罩和帽子,用瞪得快要掉出眼鏡的那雙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沒有任何感情波動地說:「你可能是喉結核,我們這裡治不了,你去專科傳染醫院吧。」
我的心在那一刻停跳了半秒,我僵住了,直到出了醫院坐在車站旁的階梯上都沒有緩過來,一種突然的無力和失重籠罩着全身。
當天下午,我和父母一起去了省結核中心。省結核中心在城南,換了幾路地鐵又坐上鄉間大巴,我們從滿是學生的大學城一直坐到靠近山嶺的鄉鎮。在車上看着越來越少的樓和遠處越來越清晰的山脈,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要被送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了。看着不遠處那塊寫着「結核防治院」的牌匾,我聯想到的是監獄和精神病院。
「69號,在這兒。」
護士朝病房裡新加的病床一指,快速地套上被子和床單,我一臉無措地站在一旁,病房裡其他的病友齊刷刷地看着我:一個胖胖的正在吃香蕉的婦女,一個戴着眼鏡看書的學生,還有一個頭髮花白乾瘦的老人。等護士走後,她們問起我的病,我尷尬地搖了搖手,指了指喉嚨,示意自己不能說話。因為我是比較少見的「失音喉結核」病人,床頭被貼上了語言障礙的標牌。查房時醫生對我議論紛紛,護士也表現得異常好奇,每次都故意關心我一句,看看我的反應。
住院第二天清晨不到6點,被抽了有20多管血。我第一次感受到抽血被抽乾,站起身,腳像踩在棉花上,從胳膊到手都沒有半點力氣,只能躺在病床上按着棉簽一動不敢動,看着護士拿着一堆貼滿標籤的試管走了。
下午又是一波抽血,巨長的針頭扎進皮膚的一瞬間,我硬是忍住了迸出來的生理性眼淚,可結束的陣痛讓我只能任由眼淚噴涌。隔壁病床的大姐安慰我:「才開始抽都這樣,像我已經抽麻木了,腫起來了。」
在這裡,每個肺結核病人最重要的檢查標本是痰,通過查痰,可以判斷病人是否存在結核桿菌、是否處於排菌的感染期。檢查需要的是早晨從肺里咳出來的深痰,清晨醫院走廊里,患者們都在拼命咳痰,為了趕在檢查標本櫃收走前把咳好的痰瓶放好。
初來時,我接過護士遞過來的7個空瓶直發愣,用力咳了咳,只咳出來一堆唾液,咳得聲帶一陣疼。像我一樣不怎麼會咳痰、也咳不出來痰的患者很多,但咳不出痰就無法鑑別是否仍存在結核菌,醫生會安排患者做氣管鏡肺部灌洗檢查。
氣管鏡檢查是結核病院裡最恐怖的存在,很多人在前幾次都會選擇全麻或者半麻,由於麻醉的費用高昂,後期再做氣管鏡治療時,都直接局麻。聽到主治醫生給我安排了全麻後,我舒了一口氣,恐懼被「全麻之後什麼感覺都沒有」的心理暗示抵消了。
檢查當天我拿着麻藥和衛生紙走進檢查室,卻被告知喉結核因為涉及聲帶,只能做局麻。我的大腦頓時一片空白,陪着我的母親猶豫地看着我,我心一橫:「那就局麻吧。」
氣管鏡檢查室裡面圍着四五個穿着手術服的醫生,「過來,躺下」,嘴裡被噴了幾下麻藥,舌根處漸漸麻了。
「把你的口罩往上面放,遮住眼睛。」醫生助手在我嘴上鋪上一層層紙巾,在我手指上夾上心跳監控器,「平穩地張嘴呼吸。」
我跟着指令,感受到一根管子從鼻子塞進去,穿過喉嚨伸進呼吸道里——我要窒息了——局麻的作用微乎其微,我身體的瞬間反應是把插進嘴裡的管子吐出來。我開始乾嘔,嘔出來的唾液浸濕了嘴上的紙巾,護士連忙又往我嘴上鋪紙。我大口地用嘴吸氣,喘不過氣後本能地往外嘔,身體剛不受控制地蜷曲起來,又被旁邊的護士按了回去。
「哎呀,別緊張,平穩呼吸啊。」操作的醫生有些埋怨,我每一次掙扎地喘氣都導致了管子錯位,他必須要扶正再操作。
我儘量讓自己平靜下來,幾秒鐘後我感到一根插進肺里的管子吸走了些什麼,我又再喘氣,喘不過氣後又開始乾嘔……直到管子終於從我的鼻孔里拿出來,這一切才結束。
「好了,你可以起來了。」身旁的護士提醒我。
我坐起身,劫後餘生般出了一頭的汗,眼淚流了滿臉,拿着紙巾捂住正在流血的鼻孔走出操作室。推開門,母親接過護士手裡的標本,我一直在擦拭流鼻血的鼻子。回病房的路上,我看到母親哭了,可能是被我的樣子嚇到了。
檢查結果很快出來了,肺部灌洗液標本為陽性,我被正式確診為肺結核合併喉結核,開啟了漫長而痛苦的抗結核治療。
2
結核防治院建在人煙稀少的山腳下,早中晚準時紫外線殺毒。我每天早上6點多去水房接水後,會迎着有些涼意的山風站在戶外,卸下戴了整晚的口罩,呼吸片刻的新鮮空氣。
結核病是全身性傳染疾病,我和病友們患病的種類各有不同,但多多少少都感染了肺結核,因此戴口罩防止交叉感染成了一進醫院就必須遵守的規定。可即使這樣,很多患者依舊會隨便吐痰在路邊下水道里。我總是小心翼翼地繞過路上的痰液,心裡埋怨着自己說不定就是被哪個隨地吐痰的人給傳染的。
結核防治院裡的病人大多面黃肌瘦、呼吸氣短,走得異常緩慢。每天清晨都有一行人圍着醫院內院一圈圈地走,遠看過去像是一群很久沒有食人的殭屍。下午是掛「利福平(治療結核病的一線藥物)的時間,吊瓶有大有小,顏色鮮紅通透,遠看過去像是一瓶瓶血,「殭屍」們經常開玩笑說:「咱們又該補充血了。」
病友們人人抱着暖水袋,隨着天氣越來越涼,液體流進胳膊的感覺越來越明顯,我手背上一針針扎過的痕跡也越來越重疊,針孔處長了新肉,形成了一條條疤。
同病房的劉阿姨的手臂乾瘦,手扎多了針後很容易鼓包,每次護士從一號床扎到最後一床時,她就已經跑針了,只能重新紮,扎在手腕上、胳膊上,針頭就在肉皮上顫顫巍巍地懸掛着。為了防止跑針後又要重新紮針,我們在扎針前都會瘋狂地拍自己的手背,或者把手放進熱水裡泡着,讓扎得僵硬的血管暴起來。為了保持血管處於良好狀態,我每天都在手臂上貼4至6小時的醫院自製藥膏,一貼幾十塊錢,我不捨得浪費,就一直貼着,直到藥膏干硬了才取下,貼得太久,皮膚上出了疹子。
住院後期,我兩隻手背的血管已經被扎得沒了彈性,護士會直接扎到我胳膊上。技術高超的護士會扎在小血管上,針頭懸在半空中,我的手臂只能一動也不敢動地僵直着。也可以選擇在手臂上扎滯留針,但每天的護理費也遠超普通針,很多病友嘗試了幾次後便不再繼續。
除了每天必要的輸液,我還要堅持做霧化治療(將藥物經吸入裝置分散成懸浮於氣體中的霧粒或微粒,通過吸入的方式使藥物沉澱於呼吸道)。早上護士將藥放進霧化試管里後,我一隻手掛着針,另一隻手打開機器,咬着管口不斷深呼吸,藥霧包裹着我的聲帶被吸進氣管。入院時我幾乎完全失聲,醫生的那句「你以後聲帶可能恢復不了」讓我深深地恐懼,於是每次我都用盡全力地吸,20分鐘的霧化吸到最後,只覺大腦缺氧,腮幫子咬得僵硬。我想,如果每天堅持用最正確的方式做霧化治療,藥就能快點吸收,我就大概率不會變成啞巴了。
10月的山腳下已經開始降溫,國慶節連着下了好幾場雨,大部分醫生放了長假,也少了一些護士的面孔,醫院顯得有些冷清。我與外面的世界已經斷聯了1個月,躺在病床上,望着電視發呆。看着一天天往後加零的賬單,大家心裡都清楚,這醫院就像一個牢籠,囚禁着身體也摧殘着精神。靠近門口床位的女孩每天扎完針都要感慨一遍:「唉,什麼時候能出院啊,我這手腫得都跑針了。」
「忍忍吧,會越來越好的。」劉阿姨安慰她。
我的床位靠窗,每天都能聽到其他病房傳來的聲音。隔壁病房住着一個「特護」的老年病人,需要全天24小時監控心跳,安靜的時候,能聽到機器一直發出的「滴滴」聲。老人床邊經常坐着一個男孩,20歲左右的樣子,我入院幾十天,只見他一個人在,坐在病床邊,睡覺吃飯一刻也不敢離開。他一直握着老人的手,我每次經過病房門口,都能感受到他的害怕和疲憊,想必老人是他很重要的親人吧。
有天晚上護士查房查得晚,我迷迷糊糊快到12點才入睡,沒過多久,就被樓道里的動靜驚醒了——是那種病床滾輪快速推動發出的巨大摩擦聲。我聽見值班護士大聲地喊着:「呼吸!吸氣!吸氣!」
隨即傳來主任急匆匆問話的聲音,言語間的緊張徹底打破了夜晚的平靜。第二天一早,我聽到路上有人在討論昨夜的搶救,聽說是隔壁病房的老人。
我第一次感覺死亡和我如此接近,就隔着一堵牆,一道門。
後來我再也沒見過那個守病房的男孩。有人說老人轉院了,有人說去世了,流言真真假假傳得越來越悲涼。待在醫院,看到的人生百態比平時更殘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有人失聲痛哭,有人愁眉不展,有人冷漠淡然。
3
經過治療,我的聲帶恢復了一些,能發出聲音那天,我激動地說了好多話,忍着疼痛證明自己不是個啞巴。病房裡的病友都驚喜地望着我:「你能說話了?!」我感覺自己重獲新生,給我扎針換藥的護士也都激動地祝福我:「平時多吃點有營養的,體重上來了就好得更快了。」
除了掛針和霧化,我還要堅持每天吃藥。「藥不能停」在結核病院裡是每天實實在在的寫照。彩色的膠囊和各種形狀的藥片被塑封在藥袋子裡,倒在手裡一大把,有的藥片發酸,有的膠囊發臭,有時藥太多卡在嗓子裡,我灌水送藥撐得胃難受不已,吃完就已經飽了。
結核病的高消耗迫使我一邊吃大把的藥,一邊補充恢復期必須的營養。香蕉、蘋果、彌胡桃是病房裡最受歡迎的食物。醫院的飯少鹽少油索然無味,母親在醫院附近村子裡租了一間房給我做飯,是一個村民自住房的二樓,一個月500塊錢,比住在賓館裡便宜很多。
沿着窄窄的樓梯經過走廊,有個小院子,有5間房,住滿了住院病人的家屬。房間裡通常陳列着一張床和一張桌子,桌子上自己帶的鍋和爐子連着窗戶外的插線板,牆上釘着根貫穿整個房間的鐵絲,掛着毛巾和口罩。一近中午,家家窗前便開始油煙夾雜着飯香一起翻騰,味道能一直飄到村頭。
租的房子隔壁住了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叫任玥。她得了肺合併氣管結核,每天咳個沒完,說幾句話就輕輕地咳幾聲。由於順路,我和她一來二去地熟悉起來——說起來也算有緣,我倆的主治醫生是同一個。
那位叫崔敏的見習醫生,身高中等,體態微胖,戴着圓圓的金屬邊眼鏡,走起路來慢騰騰的,負責的病人大多是很年輕或者基礎病很少的中年人。她是病區里比較出名的醫生——別的醫生靠經驗和地位出名,她則是靠病人一傳十十傳百的吐槽而出名。
醫生辦公室設在一樓走廊,門口經常站滿了等待詢問病情和想要看CT片子的病人。病人們每天還沒到醫生上班的時間,就望眼欲穿地盯着辦公室的門,門推開的那一刻,如果自己的主治醫生剛好出來,就能詢問一下病情和治療安排。我和任玥也在門口等過,想要問一問各自的治療方案,崔敏總是三言兩語打發我們,清冷的聲音像是飄過來的,邊說邊退,整個人完全進了辦公室後就快速關上門,自顧自說話的聲音跟着身影消失在門縫裡。她只要看到病人探頭進了辦公室,便會直接喊道:「出去出去,別進來!」
她總是來得晚,走得早,護士們裝好吊瓶催促扎針之前很難見到她,我只能躺在病房裡扎着針等她來查房。往往快到中午時她才輕飄飄地走過來,醫生帽將頭髮裹得嚴嚴實實,面無表情地問一句:「今天咋樣啊?」然後迅速結束對話,在本上畫勾後飄走。劉阿姨和病友們有時也覺得她過於冷淡,同情地看着我:「你的醫生每次來咋啥都不說啊?」
由於病種特殊,醫生跟病人保持距離是可以理解的,但相比主任把病人帶進辦公室耐心講解,崔敏的冷淡難免讓人覺得心寒。
劉阿姨的主治醫生姓胡,是個戴黑框眼鏡的瘦高男人,每次來的時候總是笑盈盈地對身邊的助手吩咐檢查內容。劉阿姨的胃不舒服,吃不下飯,總是一遍遍地問他:「我現在為啥吃不下飯啊?我為啥會得這種病呢?」胡醫生就笑笑:「沒事,阿姨,腸胃有反應是藥物的副作用,你就安心養病,這又不是什麼治不好的病。我給你安排了這幾個檢查,檢查一做咱們看結果再看需要添什麼藥。」然後用手幫劉阿姨掖好被子,隨即取出上衣口袋的酒精朝手上噴了噴。
隔壁病床女生的主治醫生是個有些發福的大叔,他常用輕鬆的語氣安慰自己的病人:「沒事兒,沒多大的事兒,別放在心上,這是很正常的。」也會在她做氣管鏡的時候說:「你做氣管鏡局麻就可以了,因為你還年輕,全麻對身體不好。一會兒我讓護士給你把需要的藥拿過來。」
崔敏冷淡和寡言少語的風格讓病中本就敏感多疑的病人們越來越不滿,私下互相哭訴的事情不少。一次在辦公室門口的走廊里,一個中年女人對着崔敏哭得歇斯底里:「我已經等了這麼久,要到什麼時候?你為什麼不說清楚呢?」
「你不想做就別做了嘛,做檢查的錢又不是進了我兜里。你問我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氣管鏡室的人。」崔敏也不認輸,聲調揚得高高的。我和幾個病友站在一旁被她看到,她扭過頭,用有些尖銳的聲音對我們說:「看什麼看啊,別在這兒看!」
「醫生,我這個胳膊起了點紅疹子,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啊?」
「那加個過敏藥吧。」
「我最近感覺有點盜汗沒事吧?」
「那給你開個止汗貼吧。」
「我最近有點感冒,不知道會不會感染影響病情啊?」
「感冒就吃藥啊。」
崔敏不僅不苟言笑,也不怎麼說治療的安排和方案,我的聲帶沒有完全恢復,和她的溝通愈加簡短生硬,很多安排都是護士通知後我才知道的。雖然我安慰自己:沒事,只要她能治好我就好。可看着病友們與各自的醫生交流順暢,我卻對自己病情的發展充滿了擔憂和焦慮。我用一天都不怎麼說話的聲帶想要和她交流時,總是會得到冷冷的回覆。病友們有時候也會當着我面感慨:「幸虧我不是你這個醫生,要不然我要氣死了。」
我只能默默地拉上帘子,幾度控制不住地哭。我寄托在醫生身上的期望徹底崩盤,我希望聽到幾句病情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的話,哪怕是敷衍幾句,我也能用它安慰自己一整天。
住院樓的二樓是耐藥病區,這意味着這裡的病人們要承受比普通病友更高價格、更強副作用的藥物壓力。一次我去接水,經過樓梯拐角時看到一個瘦得皮包骨的中年男人縮在角落裡抽泣,我不知道他經歷了什麼,但在醫院裡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孤身一人吃飯、鍛煉、取藥,付着每天不斷增加的醫藥費。
看多了悲涼,一點溫暖都變得彌足珍貴。
我們所在的病區有一對情侶,每天在病房前擁抱,拉手去醫院的食堂,沒有因為怕對方傳染而心有芥蒂,反而每天笑嘻嘻地告別又再見。我在水房接水時看到過他們隔着口罩接吻,一旁接水的阿姨看到兩人的舉動後滿臉嫌棄。
「多大了還不知道注意,在醫院都得病了還摟摟抱抱。」
我和旁邊的女生不約而同地相視一笑,看到了彼此眼裡的一絲絲羨慕,共同經歷病痛的感情,會更難得純粹吧?
在我住院不久後,病房又住進了個藏族大姐,她的後背上鼓起了個大包,由於壓迫氣管,每次睡覺呼吸時發出像公雞打鳴一樣的聲音,有時候像是會在半夜直接睡過去。她不會說普通話,但有一個會說漢語的弟妹,和她擠在狹窄的單人病床上照顧她。她們每天刷着短視頻,裡面反覆播放着藏族歌曲,有時跟唱幾句,說着我聽不懂的語言。害怕她吃不慣醫院的飯,弟妹會在外燒好飯送進來,跟過來巡房的醫生翻譯她的病情。這樣的親情讓我觸動,想起母親給我送飯的時候——兩層的飯桶打開,裡面放着我最愛吃雞腿和米粥。看着病房裡其他人羨慕的眼神,難以名狀的感動和幸福一瞬間哽在我的心頭。
無論什麼時候,只有父母是最疼愛我的人,最關心我吃得好不好,心情好不好,身體力行照顧我。微信里都是他們的問候:聲帶好點了嗎?護士今天扎針疼不疼啊?醫生今天有沒有說你檢查的情況啊?他們是我在面對病痛折磨感到害怕孤獨時,永遠堅定地溫暖我、照亮我的港灣。我感恩他們,永遠愛他們。
4
11月的時候,我住院2個月了。期間接過一次朋友的電話,忍着聲帶的疼痛,和她斷斷續續說了將盡10分鐘的話,能簡短就簡短,能不說就不說。我不敢告訴她我生了什麼病,只說嗓子出了點問題在住院。朋友叮囑兩句叫我好好休息,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藏族大姐做手術轉院後,新來的女孩睡在了我旁邊,是個准研究生。看着每天掛着針的手,她哭笑不得:「我同學還有我們村的人都以為我已經讀研了,誰知道我在醫院天天掛針呢……」晚飯後我經常聽到她和朋友打電話:「我現在讀研時間少,就晚上有點時間……我最近沒怎麼發朋友圈……」她不敢告訴朋友自己得了結核,只好一個個地隱瞞。每次放下電話後又頭痛不已:「我恐怕出院了也回不了家,村裡的人說不定會以為我退學了。」
結核病院裡充滿了各種各樣這類謊言。
劉阿姨在家排行老五,得了傳染病害怕被家人知道,不接姐妹們的電話。4個姐妹一個接一個地給她打電話,她只好不是說自己工作忙,就是推說假日不休息,鬧出了一連串笑話,最後被識破謊言,只好哭着把實情全說了——從根兒上,我們這些結核病患者都覺得自己不是正常人,要不,誰會天天戴口罩睡覺呢?
因為結核病院沒有複查喉嚨的設備,我回了市里一次。那天下着雨,我打車往地鐵站趕,剛好趕上晚高峰,出租車堵在鄉間集市的小道上,雨水聲混在交通擁堵的泥濘里,嘈雜一片。我忍着剛掛完點滴沒有吃飯的噁心稍微把車窗搖下去了點,風帶着水汽拍打在我的視線上,斷聯了2個月的我又觸碰到這個世界了,卻覺得與之格格不入。
地鐵上一如往常地擁擠,我擠坐在座位的角落,看着地鐵上的乘客——有閨蜜聚在一起聊天的,有下班疲憊不堪的,有帶着耳機打遊戲的,有討論考研複習的。我把沉甸甸的包放在腿上,裡面裝着我的藥和病例報告。
我是回到人潮湧動的都市了,但我沒有一點安全感,我突然覺得只有醫院才是我應該待着的地方——那裡大家都有病,都不能正常地生活。我忍着飢餓感帶來的反胃,一遍一遍地把想要奪眶而出的眼淚往肚子裡吞。下了地鐵,我坐在飯館裡開始哭,控制不住地大哭。可能是太餓了,又或者是被刺激到了,我指着菜單上的飯示意着服務員,卻聽到他們在低聲討論我一定是談戀愛被甩了。
硬是混着眼淚把飯吃完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哭得忘乎所以。
11月過半,我的聲帶又恢復了一些,已經可以長時間正常說話了,喉鏡檢查的結果顯示,「新生物」已經消失,緊接着我又被安排做了氣管鏡。
崔敏讓我填告知單的時候給我寫了「全麻」,我抬頭對她說:「我要做局麻!」
「局麻?」
「麻醉師說喉結核不能做全麻。」
我比上一次檢查更緊張。我坐在檢查室門口的走廊里一遍一遍告訴自己:你已經有經驗了,一定會比上次更加輕鬆。但當我躺在操作台上的那一刻,心卻狂跳不已,身體抑制不住地發抖。被口罩遮住眼睛的我,在迷糊中聽到身旁的醫生說:「你緊張幹啥嘛,心跳跳那麼快。」緊接着又是窒息般的吸氣乾嘔,我不由自主地蜷起身體,「不要動!不要動!我給你上藥呢!」掙扎間我緊緊抓住了護士按住我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快好了,快好了……」她安慰我道。我眼淚縱橫,心裡祈禱着再也不要做氣管鏡了,再也不要。
這次氣管鏡檢查過後沒幾天,我的痰檢被告知呈陰性,終於被允許出院吃藥治療。辦理完出院手續,我和病房的病友告別,大家都互相許願說和醫院再也不見。
11月末的天氣已經徹底涼了下來,我穿着羽絨服打車回家的時候夜風習習,望着窗外家家戶戶點起的燈火,我心裡雀躍不已。
我回家了,我終於逃離那個可怕的地方了。
| 省結核病院(作者供圖)
5
從醫院回家後,我依然是被隔離的對象,在家一直戴着口罩,吃飯也單獨在自己的房間裡,每天用紫外線燈做着消殺。我自認為是個積極陽光的人,但養病期間令我「破防」的事卻時時發生。
「破防」的主要原因是同輩間的壓力。之前我是朋友們的情緒垃圾桶,有什麼煩惱他們都和我說,我也能積極回饋鼓勵。但現在,他們發消息和我說起職場、讀研、情感壓力,我通通都不想回復——只要健健康康活着都已經是最幸福的事了啊,我沒有多餘的心力去安慰任何人,於是主動和他們斷聯了。想到已經工作的朋友經歷職場獲得了經濟獨立,考研的朋友提升學歷鑽研知識去了,而我還在每天與病魔鬥爭,就對襲擊身體的各種反應誠惶誠恐。
過年期間我幾乎抑鬱了,桌子上的一排藥換了一瓶又一瓶,我每天都面無表情地吞下一把膠囊。長時間吃有毒性的藥讓我的身體苦不堪言,胃出現了問題,每天吃完藥都疼得要裂開,半夜也會疼得醒過來,輾轉反側間心臟也疼得更厲害。吃不下油膩的東西,看不了世界的美好,我的身體和心靈都疲憊不堪,一到夜晚就恐慌,開始害怕睡覺。
除夕當晚,全家人各自在房間吃完飯,我坐在沙發的一角遠遠地看着春晚,自動與其他人隔開距離。一年過去了,又是新的一年開始,一切會好起來嗎?我不知道。
零點的爆竹和煙花聲突然變大,我複製着「新年快樂,祝你健康平安快樂」給我通訊錄里的每一個人。有的人回了,有的人悄無音訊。朋友發消息說:「大年除夕我又要熬夜了,昨天熬到3點,今天不知道要幾點。」我回她:「少熬點夜吧,熬夜傷肝時間長了不好。」她回我說:「都熬習慣了啊哈哈哈,你咋這麼養生?」
確實,健康是在平時正常人的許願清單最微不足道的願望。不知道他們會怎麼看待我的祝福,但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不要體會到生病的痛苦。
2021年4月,春天來了,風都暖了起來。我看了一部叫《天賦異稟》的紀錄片,講述來自全球各地患有罕見疾病的人的故事,這些人生來就面對着常人無法想象的困難,卻依然勇敢樂觀地活出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嚴重到睡覺都需要機器維持的患者,他讓我聯想到了每天不敢睡覺的自己,看着他帶着呼吸面罩艱難地喘氣,我突然覺得,相比於他,我的病又算得了什麼呢?一個連睡覺都無比艱難的人依舊這麼樂觀堅強地活着,我一個可以治癒疾病、只是現階段停滯不前的人有什麼理由鬱鬱寡歡呢?
從那之後,我迫使自己下樓曬太陽。春日陽光溫暖和煦,白雲軟成溫柔的糰子,連成片的粉色桃花和從石縫裡鑽出的小草讓一切都生機勃勃。我在公園裡看到一個腿腳不好的女孩做康復訓練,雙手支撐着鐵架一步步挪着向前走。猛然想起《有匪》裡謝允對阿翡說的:「你手握利器,只要刀尖向前就能披荊斬棘,這還不夠幸運嗎?」
是啊,有為美好未來拼搏的資格,本來就是一種幸運了。活着,才有希望,活着,不就可以期待美好嗎?既然現在人生已經跌入低谷了,那之後的路怎麼走不都是向上嗎?
我開始按着菜譜學着給自己做飯,讀了在書架上沒開封過的書,學了一直想嘗試的尤克里里,等到斷斷續續能彈上幾首曲子的時候,已經過了炎熱的夏天。
2021年9月中旬,我與這個世界整整斷聯了一年。醫生看過了檢查結果後宣布:可以停藥了。
當天晚上,我吃了一年都沒敢碰的魚,買了樓下花店剛到的向日葵,發了一年沒怎麼發的朋友圈。朋友私信我打趣:「好久沒見你冒泡了,原來你還健在啊。」
是啊,我一直都在。經歷了一次有點不敢回憶但永遠記憶猶新的病痛折磨,經歷了一次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停滯,明白了不管經歷什麼苦難,只要這個世界依然存在,愛你的人依然存在,你對美好的嚮往依然存在,就永遠不會與這個世界斷聯。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編輯 | 牛嘉宇 運營 | 梨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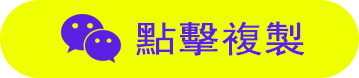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情感方面有問題,真的是要找專業的諮詢機構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