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羅斯傳》:菲利普·羅斯的生命、文學、性
2021年4月,由布萊克·貝利撰寫的《菲利普·羅斯傳》(Philip Roth: The Biography)問世。此時離羅斯去世已經過去了大約3年。這本厚達900頁的傳記由50個章節、6個編年部分組成,詳細講述了羅斯的痛苦而崛起的一生。中文譯本不久將由「99讀書人」推出。
在某種意義上,羅斯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白人男性作家。在55年的創作生涯中,羅斯寫了31本小說,其中大多以其家鄉新澤西州紐瓦克為背景,故事情節涉及猶太人的生活和身份認同,以及性描寫和性哲學。
菲利普·羅斯羅斯的輝煌開始於《再見,哥倫布》(Goodbye, Columbus),二十六七歲的羅斯憑藉他的第一本書獲得了1960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當然彼時的國家圖書獎尚沒有今日如此之大的聲譽和決斷權。發表於1969年的《波特諾伊的怨訴》(Portnoy’s Complaint)則代表着羅斯文學的第一波高峰。小說通過中產猶太人與心理分析師的對話,講述了主人翁迷戀性事、對性慾的追求及性困惑的往事。隨後,羅斯捲入對他的批判風波中。以虛構人物內森·祖克曼為主角的一系列半自傳作品則標誌着羅斯的第二波高峰,它們主要集中在1979年到1986年間。第三波高峰則是美國三部曲,《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給了一個共產主義者》(I Married a Communist)、《人性污點》(The Human Stain)。2012年,羅斯向一位法國記者表示,他不再寫作了。「和寫作進行的搏鬥結束了」,羅斯把這句話貼在了電腦上。從此,羅斯就再也沒有寫過任何作品。我已經不再擁有足夠的思維活力或身體精力來支撐我進行寫小說這一內耗巨大且複雜的過程了,」羅斯表示,「每一種才能都有它的期限、生命周期和維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一直保持高產。」在55年的作家生涯里,羅斯日復一日地面對空白的頁面,在寫作中抵抗人生,並進行自我保護。在總結過往的經驗時,羅斯說,「振奮與沉吟,沮喪與自由,激情與不安,豐盈與空虛,挺進與踉蹌——每一天我都在這些對立與矛盾之間不斷地震盪、搖擺。當然,還有深邃的孤獨和沉默:五十年如一日地在寂靜的房間裡,猶如在海池的深底,努力捕撈勉強能夠成文的字詞和話語。」

就在同一年,布萊克·貝利(Blake Bailey)授任成為羅斯的傳記作者,或許更為卓越的作家赫敏·李和朱迪思 ·瑟曼則拒絕了羅斯的邀請。在正式的會談和面試後,貝利獲准查閱羅斯的所有檔案,包括那些最為私密的。這隻從樊籠中飛出的鳥,再一次藉助傳記作家之手吐露了出自己的語言。
和眾多經典作家對傳記的迴避不同,羅斯一生都很青睞傳記,他自己在不同的時期創作了幾部傳記作品,其中包括《遺產》《事實》,後者在相當程度上對真實的歷史進行了杜撰。顯然,羅斯是整個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特殊例子,像我們所熟知的經典作家,諸如查爾斯·狄更斯、沃爾特·惠特曼、亨利·詹姆斯、西爾維婭·普拉斯等等作家,為了逃避傳記,都毀滅了他們的信件、日記,以及任何他們能找到的傳於後世的私人片段。而羅斯為所有人開放了他的全部檔案,當然僅有少數幾個人可以查閱這些檔案,其中接觸這些檔案最多的就是貝利。
從歷史上說,美國傳記的傳統非常貧乏,與之對照的是,英國傳記傳統一以貫之的深厚和富足。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在二十世紀崛起了如此之多的經典作家,而他們竟然無法見諸於僅僅一部優秀可觀的傳記作品中,科馬克 · 麥卡錫(Cormac McCarthy)、 e.l. 多克托羅(e.l. Doctorow)、唐 · 德里羅(Don DeLillo)、托馬斯 · 品欽(Thomas Pynchon)等人甚至都沒有傳。貝利的傳記生涯很短,但他卻日益拔出單薄的美國傳記傳統。貝利是《誠之悲劇:理查德·耶茨傳》(A Tragic Honesty: The Life and Work of Richard Yates)、《契弗傳》(Cheever: A Life)的作者。這兩部作品也為貝利奠定了聲譽。
羅斯,為所有人所知的形象是,性慾旺盛、憤怒無情、受害感十足但很乏同情心、自我辯護的花花公子,而這也是貝利的羅斯。在這本羅斯傳中,貝利和他的傳主羅斯,從未希望這本傳記能夠為他從前的生活辯護。羅斯告訴貝利,他只需要讓他變得有趣就可以了。為了使羅斯變得有趣,他的性經驗和文學上的抗爭被凸顯了出來,而它們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那麼顯著。
性生活和欲望,一直以來都是占據了羅斯形象的核心,這也是他作品的核心元素。在出版《波特諾伊的怨訴》後,羅斯收穫了巨大的聲譽,並開始逐漸遠離當初的單調生活,徹底變成了一位響噹噹的花花公子。通常情況下,羅斯白天寫作,晚上和一位接着一位年輕女孩追求性快感。在1975年,貝利寫道,一位賓夕法尼亞女學生為這位學者和作家深深迷戀住,他們走到了一起。在羅斯的指導下,這位女學生學會了如何正確地口交,同時,羅斯陪同她去慶祝聖誕節,並輕而易舉地替她還清了大學貸款。這段短暫的戀情只是羅斯諸多戀情中的一例。
和英國女演員克萊爾·布魯姆(Claire Bloom)的戀情開始於1976年,他們往返於康涅狄格州、紐約、倫敦進行各自的工作,和演員、藝術家、作家們交往,其中就有哈羅德·品特。漫長的交往和短暫的婚姻以雙方相互間的指責而結束。而這二十年,正是羅斯的布魯姆時代。1996年,克萊爾寫了《離開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 ,她充滿憤怒地指責羅斯過於自私和厭女。為了回擊,羅斯也完成了一本傳記,並請律師審視自己的檔案和手稿,但這本書最終在朋友們的勸服下草草收場。
羅斯的性遭遇在祖克曼身上擴大了。作為一個虛構人物,祖克曼或許遠比羅斯更為和諧和豐富。祖克曼,被羅斯渲染成一個激進的自由實踐者,他公然捍衛性的瘋癲,並與其最醜陋的一面作鬥爭。祖克曼寫了一本叫做《卡諾夫斯基》的小黃書。在所有這些故事中,祖克曼被責備說是個態度冷淡、樂善好施、盲目樂觀的特權階層新教徒。祖克曼身上的邪惡,在羅斯更為廣闊的書寫中,變成了一種美德,而這經常被嘲笑為「美德騙局」,尤其是那些女權主義者。如我們所料,晚年的祖克曼患上了前列腺癌,身體和創造力都消耗殆盡。祖克曼定期去西奈山醫院看泌尿科,寄希望於保持身體的潔淨、更換特質的內褲,來挽救這樣的緊急狀態,他再也無法回復他的青年狀態。祖克曼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焦慮,傳記作家有可能會顛覆他的過去,扭曲他想象到的正義。在他看來,傳記作家只是試圖將藝術削減到可以理解的限度,在這種情況下,小說被故事取代了。
《菲利普·羅斯傳》「在這幾十年裡,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了一群感到困惑與不安的男人,他們被性慾所控制,同時又努力地與其進行調和,以期找到一種平衡與滿足。在描繪這些男性時,我努力嘗試復原他們最本真的面貌:他們的行為、所經受的誘惑、對性慾的渴求、以及所面臨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困境。在這些小說中,我並沒有迴避男人在性慾投射的過程中所作出的一些可能會引起反感與不安的行為。我不僅想要描繪出男性在進行這些行為時的內心活動,更想要剖析這一頑固的、持續的欲望驅力對理性造成衝擊的現實情境——在某些情況下,性慾的驅力過於強烈,以至於它可能會導致理性的消退或缺席。」在一次訪談中,羅斯說道。正如祖克曼所說,羅斯的一生,藉助這本傳記延長了、現實化了。每個讀者都會見證到羅斯的年輕女友,隨着年齡增長,這些年輕女友越來越多,她們承擔了藝術家之外的生活義務,充當他的照顧者、司機、護士。由於羅斯的無所保留,貝利也記錄下來了羅斯的癖好,以及他微不足道的瑣事,比如,羅斯喜歡講笑話,討厭伍迪·艾倫,不信任心理醫生。在這些生活現象和片段背後,羅斯的更為廣闊的一面被揭示了出來,讀者被獲准進入小說背後的生活源泉,在那裡,每日有激流從岩石中流淌出來。直到那個晚年的、蒼白的羅斯,性衝動和寫作欲望都消退了,剩下的只是某種厭倦,正如他對他的孩子所說的,「我也厭倦了自己的韌性。」
羅斯的寫作恰逢美國小說最好的時代。那個時候,文學並沒有被政治宣傳、所謂的流派所玷污,也沒有所謂的地域中心、同質群體、國家團體。社會整體對文學普遍漠不關心,人們甚至沒有一點對當代文學的理解力。所有這一切給予了那個時期的作家以某種自由,文學也因此從更廣泛的範圍中生長出來。而現在,一切都大不相同了,敵意、偽善、過度操控、負債等等遍布在這個世界。在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看來,在壓抑的五十年代,羅斯逃離了諸多的形式主義、諷刺手法、間接隱喻、亨利·詹姆斯式文字,他筆下的文字瞄準了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虛偽和謊言,而其中也有我們熟知的反叛。
在《事實》中,羅斯試圖重回家園,重回原點,再次生長。對羅斯來說,紐瓦克是一個安全和平的天堂。「我並非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他的知識的表達形式就是敘事,但他的敘事內容從不豐富:家庭、家庭、家庭,紐瓦克、紐瓦克、紐瓦克,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有點像我自己的敘事。」羅斯寫道。在這部回憶錄中,羅斯用迂迴的方式對過去做出了澄清。祖克曼給羅斯來信說:
「至於特徵描述,羅斯是你所有主角中被描繪得最差勁的。你的天賦不是讓你的經歷個性化,而是人格化,即讓一個他者來體驗你的經歷。你不是一個自傳作家,而是一個人格化作家。與大多數美國同代人不同,你的經歷是逆向的。你對事實的熟悉和感覺,比不上你對小說的理解和權衡。你能讓一個虛構的世界比它所依據的真實世界更令人興奮。我的猜測是,你多次創造了自己的蛻變,以至於不清楚自己現在或曾經是誰。時至今日,你已變成一本行走的書。
你在此講述的求學史——奔赴外面的大世界,告別自己的小圈子,讓自己撞得頭破血流——與有關我的成長小說相比,並沒有顯得更加密集緊張,或更加歲月崢嶸。唯一的例外,是你在婚姻中所承受的折磨。你指出,類似的經歷最終成為我不幸前任塔諾波爾的命運,我因此而對你感激不盡。但在猶太人反對我寫作方面,我謹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像你的家人一樣,對我的職業沒有如此強烈的反感。」
葡萄牙語譯者瑪格麗特·胡爾·科斯塔:科斯塔和她的翻譯帝國
作為一名資深的葡萄牙語譯者,瑪格麗特·胡爾·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已經翻譯了超過130多部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作品,其中包括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埃薩·德·凱依羅斯(Ea de Queiroz)、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António Lobo Antunes)、克拉麗斯·利斯佩克托(Clarice Lispector)、保羅·柯艾略 (Paulo Coelho)、路易斯·費爾南多·沃瑞西莫(Luis Fernando Verissimo)、莉迪亞·豪爾赫 (Lídia Jorge)、特琳達·格桑(Teolinda Gerso)等葡萄牙語作家的作品,以及拉斐爾·桑切斯·費爾洛西奧(Rafael Sánchez Ferlosio)、拉斐爾·奇畢斯 (Rafael Chirbes)、哈維爾·馬里亞斯(Javier Marías)、阿爾瓦羅·龐波 (lvaro Pombo)、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路易莎·瓦倫祖拉(Luisa Valenzuela)、安吉拉·瓦爾維(ngela Vallvey)、恩里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貝爾納多·阿查加(Bernardo Atxaga)等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其中恩里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的寫作語言是加泰羅尼亞語,貝爾納多·阿查加(Bernardo Atxaga)的寫作語言是巴斯克語作家。這份名單雖然沒有涉及全部重要的葡萄牙語作家,但是卻零散地統攝了近兩百年的葡萄牙語文學的歷史。科斯塔,是歷史上最多產的譯者之一,她也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葡萄牙語文學譯者。
瑪格麗特·胡爾·科斯塔「我願意把自己想象成翻譯界的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我剛在《小婦人》中看到了斯特里普女士,她非常特別。她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神、每一個手勢,都是完美的。」此前在回應《巴黎評論》的訪談時,科斯塔表示。的確,科斯塔和斯特里普一樣,都追求完美。訪談發表在《巴黎評論》2020年夏季刊上,為「翻譯的藝術」系列第七篇。按照順序,「翻譯的藝術」此前有,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譯者羅伯特·菲茨傑拉德 (Robert Fitzgerald)、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譯者羅伯特·法格勒斯 (Robert Fagles)、意大利語譯者威廉·威弗 (William Weaver)、俄羅斯語譯者理查德·佩維爾(Richard Pevear)和拉里薩·沃洛克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夫婦、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譯者彼得·科爾 (Peter Cole)、德語譯者邁克爾·霍夫曼 (Michael Hofmann)。作為一個卓越的葡萄牙語譯者,科斯塔直到18歲才觸及到葡萄牙語的邊界,且還是在哥哥的引導下在西班牙接觸到了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當然,科斯塔最初接觸西班牙語的說法有很多,但它們都有一個基本事實,直到18歲,科斯塔才接觸到了西班牙語以及少量葡萄牙語。在24歲入讀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後,科斯塔本來要學習加泰羅尼亞語,西班牙語幾個自治區的官方語言,隨後就轉為葡萄牙語,據說是受了巴西電影《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的感召。翻譯家和老師菲爾 · 波蘭克對科斯塔有着很大的鼓勵和標杆作用。在後來的生命中,西班牙語的權重逐漸降低,葡萄牙語的權重則逐漸升高。在科斯塔看來,西班牙語相對外向,而葡萄牙語相對內向,一個內向的語言,對科斯塔的吸引力更強。科斯塔認為,她切換到西班牙語時,會感受到詞語的限制、發音的侷促,而當她切換回葡萄牙語時,她會感受到鼻音、內向,以及一種全新的開闊。
在正式成為翻譯之前,科斯塔做過速記打字員,而後去布里斯托大學、斯坦福大學讀書,畢業後相繼在一家倫敦書店、科英布拉大學工作,後來還做過詞典編纂。這份極為特殊和挑剔的詞典編撰工作,教會了科斯塔很多,她不得不應付例句、含義等等詳細周全的安排。直到1983年,科斯塔經手了《格蘭塔》編輯比爾·布福德所委任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篇作品,《在加利西亞看雨》(Watching the rain in Galicia),這是科斯塔譯者生涯的最初開端。
科斯塔最早翻譯的作品包括阿爾瓦羅·龐波的《大房子的英雄》(The Hero of the Big House)、哈維爾·馬里亞斯的《靈魂》(All Souls)。從此之後,科斯塔成為了一個正式的譯者,並逐漸翻譯了超過100本的作品。科斯塔最早一本葡萄牙語翻譯來得稍微晚一些,佩索阿的《惶然錄》(或譯《不安之書》),這是她第五本譯作。在翻譯這本重要的葡萄牙語作品時,科斯塔當時的生活感受正好和佩索阿的碎片風格相符合。倫敦Half Pint Press出版商曾經製作出一個限量的《惶然錄》版本,碎片被印刷在紙袋、索引卡、鉛筆上,而它們又被一股腦兒地裝進紙箱裡,這個創意深得科斯塔的心。
翻譯就是寫作。翻譯不是在白紙上重寫,譯者習得自己的語言,擁有自己的記憶,這些記憶會在翻譯中釋放出來,提及翻譯觀念時,科斯塔如是說。翻譯過程,在科斯塔看來是很詩意的,它是和作者合作和交流的過程,這就好像是,譯者吸收了作者的語言和詞彙,這也就是說,作者和譯者很可能是孿生的。這幾乎是所有翻譯觀念中,最簡約、最及人的一種。科斯塔對翻譯實踐的重視要大於一切,在她看來,翻譯既不是單純的歸化,又不是單純的異化,而是在歸化和異化之間來回擺動。上述翻譯觀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科斯塔的開放、以及得乎其中的寫作經驗,這一點可以從她一直以來沒有放棄詩歌可以看出來。
科斯塔認為,不能被翻譯的詞彙和概念比人們所想象的要少得多,像Saudade這樣多義如六瓣雪花的詞彙很少,Saudade的含義里既有快樂的成分,也有憂鬱的成分,但這並不代表Saudade的含義在特殊的語境中是無法被估量的。之所以有信心說,翻譯才是可能的,是因為科斯塔對翻譯的想象是帶有語境意識的。在翻譯東帝汶作家路易斯·卡多佐(Luís Cardoso)的回憶錄時,科斯塔就跟隨着作者補充了很多東帝汶的知識,而知識又在翻譯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語境的改變和擴展,是譯者對語言的認知發生了質變的結果。「經驗告訴我,極限是可能的,它並不瘋狂,卻時常是彬彬有禮的。」
在翻譯阿西斯和安圖內斯的作品時,科斯塔不得不應付他們冗長的句子,以及他們看似晦澀的表達,尤其是安圖內斯。他們的敘述和他們的作品,一樣都是偉大的,這對任何譯者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戰。困難不止是,馴化英語適應安圖內斯看似詰屈聱牙、實則精湛深刻的表達,困難還有如何找到一種令人信服的語言,表達安圖內斯的葡萄牙語,以及它內里的超現實主義色彩。科斯塔認為《在世界盡頭的土地上》是一次進入黑暗中心的旅行,它極其殘酷,小說在崩塌中享受着狂歡,而這本書也是科斯塔最新的譯作。安圖內斯是精神病學出身,他在六十年代參與過對抗薩拉查獨裁統治的學生運動,在七十年代初期以隨軍醫師的方式被派往安哥拉戰場。安圖內斯的作品不拘泥於傳統,甚至不拘泥於現代主義,它們大多從一個更當代的創想出發,突破了確定的類型和敘事的限制。在《閱讀我的處方》的一文中,安圖內斯告誡讀者:「你們需要陷入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經心、暫停和冗長的省略,沉溺在陰影覆蓋的波浪搖擺之中,一點一點地,文本就會把你們帶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見,這對精神的再生與革新至關重要。你們需要在一頁頁的閱讀過程中失去對共同價值的信心,讓我們虛偽的內心一致一點點失掉它本沒有、但我們賦予它的意義,才能讓另一種秩序從這種衝擊中誕生,這也許會苦、會痛,卻不可避免。」
科斯塔的工作相當原始、細緻、質樸。通常,科斯塔會進行十份左右的手稿,才會得到最終的文本。前兩遍,科斯塔根據原書稿,做一遍梳理和翻譯,成稿打印出來。接着,她會在成稿上整理和修改三四遍。再接着,她會反覆朗讀,訂正,大概三四遍。最後出版社的編輯又會做出相應的反饋。科斯塔很喜歡不斷的朗讀,這會讓她更容易發現錯誤和不恰當。為了應對反覆操作帶來的磨損和增添,科斯塔不得不在草稿中留下很多空白,這已經是一個習慣。科斯塔的丈夫通常是文稿的第一個讀者,甚至可以說是前讀者,他不會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很方便為她糾正錯誤或歧義。她依賴打字機,而不是電腦,但她也逐漸學會用電腦,以輔助翻譯的進行。電腦,對科斯塔最重要的作用是,取代了原來的圖書館,將繁瑣的資料查詢工作削減到最低限度。隨着,資料庫的更新替代,科斯塔已經很少再查閱書架上的字典,除了柯林斯和牛津的兩本西班牙語英語字典。
好的翻譯必須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聲音,科斯塔此前對紐約時報說,這樣讀者才會對此感到信服。好的翻譯需要準確和忠實(不管這意味着什麼),譯作應該和原作一樣同樣也是傑作。準確、忠實、傑作般的質地,這是科斯塔一直以來的追求。迄今為止,科斯塔收到的最大肯定來自馬里亞斯的研究專家,他說他從閱讀英譯本中獲得了很多樂趣,這並不亞於他從原本中所獲得的。
作為一個讀者,科斯塔鍾愛埃薩·德·凱依羅斯(Ea de Queiroz)、安娜·路易莎·阿馬拉爾 (Ana Luísa Amaral)、安娜·特蕾莎·佩雷拉(Ana Teresa Pereira)的作品。在科斯塔的心中,埃薩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要遠遠高於巴爾扎克,這並不是一個幼稚的看法。安娜·路易莎·阿馬拉爾是波爾圖大學教授,比較文學研究者,詩人。安娜·特蕾莎·佩雷拉出生於1958年,其作品和葡萄牙的當代變化有着強烈的共振。科斯塔最喜歡的一本書是胡里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的《濟慈的幻象》(Imagen de John Keats)。科斯塔最喜歡翻譯是阿奇博爾德·科爾昆(Archibald Colquhoun)所翻譯的蘭佩杜薩的《豹》,路易絲和艾爾默 · 莫德(Louise and Aylmer Maude)所翻譯的托爾斯泰,以及備受詬病的海倫·洛-波特(Helen Lowe-Porter)所翻譯的托馬斯·曼。目前,科斯塔正在與另外一位譯者合作翻譯佩索阿的朋友詩人馬里奧·德·薩-卡內羅(Mário de Sá-Carneiro)的作品。
在翻譯中,科斯塔委身成為一個小我,以使作者和作品的能量得到最大的釋放。「於是我們奮力前進,卻如同逆水行舟,註定要不停地退回過去。」如同科斯塔所愛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結句所道出的,卡斯塔不斷創造着屬於這個世界的奇蹟。
保羅·索魯的世界旅行
在最新作品《懷梅阿的海浪下》(Under the Wave at Waimea)中,保羅·索魯講述了一位衝浪者面對衰老、特權、死亡的故事。小說發生在夏威夷海岸,索魯回顧那一代輝煌的過去,也回應着當下突如其來的變遷。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去涉足另一種經驗,去和另外一個人相遇,索魯這樣告訴紐約時報。在日漸蒼老的這幾年,索魯仍然保留着旅行的習慣,他仍然把自己定位為強悍的旅行家。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一種尖銳的語調、犀利的觀察滲透在字裡行間,真理裹挾着謬誤鋪展在讀者面前。
《懷梅阿的海浪下》索魯最重要的一部遊記《在中國大地上》去年年末已由後浪出版。《在中國大地上》就是索魯的線性文體的標本。索魯為讀者更為自己製作了層次分明的文件有,第一個分類方法是,按照列車,也就是目的地,接着第二個分類方法是,按照故事、人物,每個故事或人物通常有一小節。單獨看每一節,其實就是索魯的模式化線性書寫,儘管他製作了上百個文件單元,《在中國大地上》的線性方式仍然沒有任何改變。在長達12個月的旅程中,索魯搭乘了近40趟列車。車速大約每小時30英里,剛剛好足夠索魯領略窗外的風景,那些稻田和山陵。在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上,索魯穿着睡衣在一幫沉睡的維吾爾族人當中走來走去,偶爾會花十便士喝杯啤酒。索魯的中國就像馬可·波羅的中國一樣,和真實的中國相去甚遠,這並非因為兩者沒有展示足夠的信息,而只是因為他們論證他們的預想或者推翻他們的預想。對於他們來說,中國就在那裡,只要去觀看和體驗就夠了,事實上,這遠非文學,文學關乎發生、成長,而非一直在那裡的東西,文學要穿越時空來到新的世界。梁啓超對此有很深的體悟,「國中那些老輩,故步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沉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
「旅行文學必須以滑稽離奇的敘事為發端,然後從新聞式的報道轉向虛構的故事,接着就以日本回聲號列車的飛快速度抵達自傳這個終點……陌生城市裡千篇一律的酒店房間把人們推向了自白模式。」在《火車大巴扎》裡,保羅·索魯提供了一種中間狀態的旅行文學定義。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索魯稱旅行文學是自白。旅行文學是自白嗎?答案或許是否定的。索魯將旅行文學推向自白的原因又是什麼?答案並非那麼不言自明。但個中緣由,絕離不開兩個,一個是文學永恆的主體性傾向,一個是索魯未完成的文學,令其不得不強化生活中自我的那一面。由此,我們大可以將索魯的旅行文學視為永遠在路上、在完成的自我敘事,它始終遊走在文學的邊緣,卻恰切地呈現了何為書寫。
索魯從未有過關於旅行文學的完整想象,他逼近這一下想象最好的方法是列清單。在答《紐約時報》的訪問時,索魯給出了自己的旅行文學推薦書單,包括阿普斯利·切里-加拉爾(Apsley Cherry-Garrard) 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威爾弗雷德·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的《阿拉伯沙漠》(Arabian Sands)、麗貝卡·韋斯特的《黑羊與灰鷹》 、伊本·白圖泰的《伊本·白圖泰遊記》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鬱的熱帶》。在《旅行之道》中,索魯列了多達十幾個清單,其中最重要的是何為好的旅行家,以及何為好的旅行文學。在索魯的想象中,好的旅行家,總是那些行將寫出好的旅行文學的旅行家,諸如塞繆爾·約翰遜、馬克·吐溫、芙瑞雅·斯塔克、伊夫林·沃。
旅行和文學的結合是自然而天然的。就像索魯暗示的,旅行文學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自我抒發的部分,儘管索魯在《在中國大地上》從未實現過這一點。蘇珊·桑塔格在《對旅行的反思》中提出,十八世紀是旅行故事、遊記小說、離奇傳說最為興盛的時期,諸如《格列佛遊記》,這些文學作品通常是第一人稱,並訴諸理想社會和異域想象。桑塔格的錯誤在於,她過度倚重了對體裁,以及敘述和被敘之間的距離的判斷。桑塔格對旅行文學的現代性的判斷極其「約定俗成」,現代性變成了對異域、殖民的克服,對想象、理解的親和,實際的區分並非如此武斷。看看索魯的說法,「相異性有時像是一種疾病;身為陌生人,近似於體驗某種瘋狂——一切熟悉的東西盡被剝奪,陌生與瘋狂暗示了同樣的不現實、非理性。」
桑塔格也會贊同的是,好的旅行文學是對現場的出走,朝着美好的歷史、未來,虛弱或豐沛的地理走去。旅行界身於現代性辯證法的邊緣,它吸引的是霍米·巴巴所說的雜粹(hybridity)和居間(in-between)。索魯對記者表達了旅行書寫之難,「在最好的情況下,旅行類型一直都很困難,它不是一場歡鬧的嬉戲,而是一次痛苦的發現之旅。今天,地球變得越來越逼仄,人口越來越多,越來越骯髒,觀光者越來越瘋狂,紙杯蛋糕越來越少,奢侈品和土著越來越少。」土著和想象存在之處,就是旅行抵達的地方,而土著和想象總是從自我出發,區別於自我的那一種,它與其說是被現代性拋到了邊緣位置,不如說被主體拋到了邊緣位置。現代性從不生產或毀滅土著,生產和毀滅土著的是主體。
「旅行文學未來的形式可能是旅行博客,包含各種省略的表達方式、口語詞彙和閒話式的意識流。」索魯說。他進而提及傑茜卡·沃森(Jessica Watson)的書寫,「下面這張照片拍的是我超酷的新T恤,放在我剛拆開的食品袋裡,是媽媽送給我的禮物。」其實,索魯只是潛在地認同瑣碎的表達,它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了某種主流。根本沒有一種旅行文學的改變,被改變的只是曾經優雅的旅行文學在今天越來越稀少。
在索魯大多數作品裡,語言的媒介是二十世紀末誕生並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主流的計算機。它比紙刊媒介、廣播媒介要快速得更多,也要清晰得多。快速使得語言退回到我手寫我口的位置,這也是為什麼索魯如此強調自白和自發性的原因。清晰則使得索魯以一種機械化的方式解決複雜的文體問題。索魯經常使用的策略是,用模式化的方式,將自我感悟、場景、對話、史料以極其簡單的方式穿插編織在一起。在索魯那種著名的影像中,在一截火車車廂里,他身形傴僂,整個兒地專注於眼前的電腦,這和E. B.懷特那張安寧、豐富的影像多麼不同。
這一切都在說明,索魯是如何把旅行變成觀光的。芙瑞雅·斯塔克曾告誡,「一個人只有敞開心扉,接受每個地方現有的面貌,不試圖把它據為己有、改變成合乎常理的、為自己所用的形態,那才是真正的旅行。」或者像《伊本·白圖泰遊記》中所經受的啟迪,白圖泰在尼羅河看見一條鱷魚,離岸不遠。有一天,他口渴,朝河裡走去,呵,一個黑人過來,站在我和那條河之間。後來,白圖泰被提醒說:「他這麼做完全是為了保護你,把自己置於你和鱷魚之間,阻擋它攻擊你。」
曾是索魯的老師和密友的V.S.奈保爾——在烏干達,索魯遇見了奈保爾,並幫助他生活,而奈保爾增強了他寫作的決心,但他們的關係後來破裂了——在《我們的普世文明》中提供了隱藏在索魯的旅行文學的背後的文本,它是精神的旅行,而非肉身的旅行,「於是,當巴基斯坦人告訴我,伊斯蘭教是一種完整的生活方式影響着每一件事情的時候,我不僅開始理解他們在說什麼,還開始理解——儘管我們可以說擁有共同的次大陸起源——我所走過的是不同的旅程。我開始形成一種關於普世文明的觀念——在特立尼達長大的我生活在其中,是其中的一分子,卻並沒有清醒的自覺。」
在所有這些旅行文學之路中,索魯選擇了那條導遊冊的道路。索魯是否認為自己是計算機時代的華茲華斯,兩者的區別僅僅在於,華茲華斯的視野是湖區,而索魯的視野是火車抵達之處。這也是為什麼索魯的旅行文學被自己稱作「轉動絞肉機的木製曲柄」的原因。索魯無法忍受奈保爾的固執,忍受那些精神探索者隨身攜帶的固執。
在開往廣州的快車上,同行的莫托爾談起了華茲華斯的《遠行》,「遠行的旅人喲,笑得真燦爛……」,索魯從未感受到如此理解他從倫敦來的同行者。躺在床上,索魯開始思考,為什麼中國會給他們留下這麼多的刻板印象,「人們很難擺脫關於它的想象,因為也難以看清真相。」很難說,索魯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答案,尤其是在2021年來看。但當他說起未來的中國將面臨老齡化的問題,及其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放棄的「失落的一代」,我們仍然會折服於他。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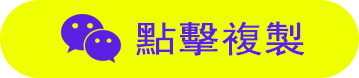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每次有疑惑都會請教,你們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謝謝!
可以幫助複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