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民警在實施抓捕行動。由於車廂擁擠,民警計劃留一人在站台,把另一名民警推上車,在車上繼續跟蹤。/ 圖片由受訪人提供
2020年7月3日,成都地鐵,一名男子猥褻女乘客時被他人制止,該男子不承認並張口罵人,最後被其他乘客群毆。報警後,這名男子因猥褻被行拘15天。對於地鐵和公交車上的性騷擾問題,如何取證,如何懲罰嫌疑人,如何保護受害者,如何防微杜漸,一直是個難題。僅2019年一年,北京地鐵就抓獲了285個色狼。中國教育里長期缺乏性別平等的內容,或許是讓性騷擾行為不斷滋生的深層原因。
「你最想得到哪方面的性別知識?」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和李嘉誠基金會合作,在全國高校做了一個面向女大學生的抽樣調查。對這個問題,收到的回答中最多的是:想了解怎麼建立性別關係;還有,性騷擾到底是怎麼回事?

2020年年初,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了一場名為「性別平等、性騷擾與情感霸凌」的講座。
這場原計劃面向校內學生的性別課程,卻意外地廣受歡迎。主講人是酈菁、尤怡文、吳桐雨,這三位浙大社會學系副教授把講座開進社會學系最大的會議室,當天人員爆滿,甚至還有人站着聽。
現場將近一半是男同學,除了本院系的學生,還有不少是從校外過來的,甚至還有幾位男老師。
在酈菁的成長經歷里,同學們普遍不懂如何建立親密關係;尤怡文則發現,至今仍有人將AV、偶像劇作為和異性相處的腳本,因此產生了不少性騷擾行為。
2017年,攝影記者余荼開始關注北京公交警方專門在地鐵抓色狼的「獵狼行動」。跟拍公交總隊四惠站派出所的過程中,余荼親歷了十多次抓捕。
他發現,在「獵狼」行動中落網的嫌疑人名單中,有博士生、銀行高管,還有兜里揣着某知名高校邀請函的CEO——此嫌疑人把車停在地鐵站附近,專門到地鐵里作案。
地鐵色狼沒有一個統一的群體畫像,也不排除有人被誣陷。/《即使這樣也不是我做的》
「還有專門抓色狼的啊」
第一次到派出所時,余荼發現裡面坐着幾名便衣警察,看起來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有的還戴着手串。
這群便衣警察的日常,就是混跡於地鐵站里的上班族之中,觀察來往乘客的動作和神態,通過一個眼神,他們就能判斷哪些人在伺機作案。
蹲守的過程枯燥無聊,便衣們就坐在車站的凳子上,或者守在車廂口、電梯口,遇到眼神躲閃的、在原地走來走去的、在電梯下面盯着人過來的,或者到了站台也不上車,在那東張西望的,「就是我們尋找的目標」。
如果一個人從一個車門繞到另一個車門卻遲遲不上車,就極有嫌疑。
2019年,北京,一位便衣警察在地鐵站蹲守。民警們只需在人群中觀察來往乘客的動作或神態,就能判斷哪些人在伺機作案。/圖片由受訪人提供
余荼第一次遇到色狼,是跟着派出所民警去西二旗拍攝早高峰擠地鐵的場景。
剛走到站台,他看見一個女孩揪着一個男人的衣領,向地鐵工作人員大喊:「流氓!抓流氓!」兩個地鐵工作人員聞訊趕來,一人架住一條胳膊,把色狼控制住。
余荼追上前拍照,那個女孩短頭髮,穿牛仔上衣和長褲,看起來就不是軟弱的性格。
讓人意外的是,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裡,余荼幾乎再沒遇到過主動抓色狼的:受害者大都不敢吭聲,甚至有人意識不到自己被占了便宜,以為只是人多、擁擠。直到色狼被抓住後,受害者才反應過來:「還有專門抓色狼的啊?」
地鐵四惠站的民警,每次幾個人一起出發,負責八通線沿線的色狼抓捕。
傳媒大學站是「色狼重災區」。遇到嫌疑人後,民警跟着上車,在嫌疑人後面拍攝證據,同時通過手機聯絡其他同事。
等列車開到四惠站或四惠東站,幾個民警從四面八方圍攏,等車門打開,嫌疑人準備離開時,民警一把摟住他的脖子。「幾個民警包圍過來,脖子一摸就帶走了。」余荼說。
女性專用車輛設立之初,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地鐵性騷擾。/wiki
「性騷擾的本質,
是某些性別對其他性別顯示權力」
去年夏天,民警在傳媒大學站抓了一個90後小伙子。他站在樓梯口,從下往上偷看女路人的裙底。看上一個穿花裙子的女孩後,他跟着女孩上了車,用拇指捅女孩的屁股。
「這種類型的人,工作中不太跟人打交道,性格上比較內向,不善言辭。通常朋友不多,沒有女朋友。這樣的人心存僥倖,一次兩次沒被抓到,覺得沒什麼事,就走上了這條路。」民警介紹說。
絕大多數被捕者會說自己是初次犯錯,也有不少人把性騷擾行為歸結為自己生活不順利——有位裝修工人聲稱丟了錢,「來泄憤」;還有人說自己被老闆批評了、和老婆吵架了,等等。
民警抓過一個小伙子,進地鐵站前就解開褲鏈,裸露下體,用書包稍加遮擋;被抓後,他說這種流氓行為讓他感到放鬆。
2018年,MeToo運動席捲全球,性騷擾與性別平等的討論在輿論場層出不窮。
這項控訴性騷擾行為的運動,隨後在學術界、公益圈、傳媒界甚至寺廟裡爆發。一直關注MeToo運動的酈菁說:「它成了一個全國議題(national issue),討論的廣度和深度是之前的單個案例完全不能相比的。」
酈菁認為,性騷擾的本質是性別不平等,「性騷擾並不是出於性需求或者性邀約,它本質上是某些性別對其他性別顯示權力的行為。只要性別不平等,權力關係依然存在,這種現象就不會消失」。
MeToo運動號召曾遭受過運動性騷擾和性虐待的女性打破沉默。/unsplash
過去,性別不平等的表現是制度化的,比如中國傳統的禮教,男人三妻四妾、女人纏足,鼓勵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男人在外工作。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展開性別平權運動之前,女性即便進入職場,也是承擔秘書這類輔助性工作。
性別平權運動後,女性可以自由進入職場,自由選擇職業。但這種源於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以更隱蔽的方式顯現,性騷擾就是其中之一。
「性騷擾很大程度上是對那些進入公共場域的女性實施的,它會給女性造成一個敵意的、有侵犯性的工作和學習的環境,目的是讓女性退出公共場域。」
余荼發現,被捕的色狼幾乎沒有共性。被抓後,有人死不認錯,有人痛哭流涕;有單身的,也有已經結婚生子的;有無業的,也有開豪車的公司老總;有沒讀過幾年書的,也有還在學校的博士生。
民警抓過一個某知名高校畢業的公司高管,此人受邀參加百年校慶,結束後開豪車專程來了趟傳媒大學站,在地鐵上性騷擾女學生。
「被警察抓住後,他還傲慢得不行:『我什么女孩沒見過?』」余荼說。
2019年,北京,四惠站派出所抓到的部分色狼,其中不乏高學歷、西裝革履、慈眉善目的「老實人」。/圖片由受訪人提供
余荼展示了他拍過的色狼,從照片上看,這些人和我們在大街上見到的沒什麼兩樣。他們看起來都挺年輕,有幾個還戴着眼鏡,看起來很斯文。
面對鏡頭,色狼們低頭認錯,不過,在這個特殊身份之外,他們是父親,是兒子,也是學校的學生、單位的員工。
「我感覺他們都是普通人,也不是罪大惡極。你說毛病也好,特別的癖好也好,反正談不上仇恨,更不能說同情。」余荼說,「你受到該受的懲罰,名譽受到損失,那是你自己惹的禍。」
即便如此,余荼也得保護他們的隱私。公開發布的照片裡,最開始是往這些人的臉上打馬賽克,警察說不行,這還能認出來;後來就給他們全身都打了馬賽克,「因為這個錯誤把人家一生毀了,也不至於」。
在印度,對女性做出對方不願意的身體接觸,可能面臨3年監禁。德國社會學者斯凡尼亞·沃爾勒曾表示,在德國,「直勾勾的凝視」也可被視為性騷擾。
但在國內,性騷擾還很難受到相應處罰。
2019年夏天,余荼跟拍出警10多次,最終被拘留的只有4個,包括用手摸、用身體頂蹭的。
警方會根據案件情節,將嫌疑人拘留10—15天,依法留取指紋等基本信息,記錄在案。不過,有些時候確實會因為各種條件限制,導致取證不足;有些情節輕微的,民警批評教育後會釋放。
2019年,北京,一名嫌疑人被帶進派出所拍照存檔。按要求,色狼們進到派出所里除了拍照、錄指紋,還要寫一份檢討書,面對「如果是你的妻子、姐妹在公共場所被別人這樣對待,你怎麼想?」的質問。/ 圖片由受訪人提供
學校不教,爸媽不談,
性別教育缺位
目前,有不少高校開設了性別平等或與女性相關的課程,課堂上,學生們可以探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在生育和教育方面遭遇的不平等。
但除此之外,酈菁發現,幾乎沒有一門課程可以告訴學生們怎麼建立親密關係、怎麼在親密關係里追求平等。「大部分課程講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但在微觀層面講怎麼實現性別的相對平等,是非常罕見的。」
在酈菁的成長經歷里,學校的教育是去性別化的。學校要求男女生穿統一校服,寬大的校服其實掩蓋了兩性的身體特徵;有些學校甚至規定女孩不能留長髮。
而在日常的教學中,老師很少提及性別問題,「把你們作為無性別的個體對待,也就是我們說的,男生女生都一樣」。
在升學壓力下,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都禁止學生們早戀,尤怡文認為:「他們不會告訴你,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該如何在不傷害對方的情況下去表達,或者當對方拒絕了你的告白時,又該如何調節自己的心情學習接受。」
因此,青少年表達情感或者追求愛慕者的方式往往是從流行影視中學來的招數。「成長中的青年男女只能依賴偶像劇或者AV影片中的情節作為生活中與異性、同性互動的腳本。」
改編自日本漫畫的《流星花園》,被稱為台灣偶像劇鼻祖,播出後迅速在亞洲各國走紅。但尤怡文認為,對於性別平等教育,這樣的偶像劇恰恰是彰顯性別刻版印象、性別階層、身體自主權的反面教材。
這樣的言語本身就在傳遞一種負面價值/《流星花園》
她舉了一個例子:公眾號「女孩別怕」曾談到一名女孩與男性室友合租,室友告白失敗,便模仿AV影片,以為只要強姦了女孩,兩人就會在一起。面對女孩劇烈的抗拒,他甚至反問女孩:你的反應為什麼和其他女孩不一樣?
「侵犯者口中所謂『其他女孩的反應』,其實都來自AV片,AV影片的公式化劇情,往往傳遞錯誤的信息,讓閱聽者誤以為『no』意味着 『yes』, 且通過男性力量,強行發生性關係,並讓對方順從。」尤怡文說。
在去性別化教育里成長起來的孩子,容易面對這樣的問題——不懂得怎樣建立親密關係。進入大學後,面臨人生的新階段,很多人會因此迷茫,酈菁發現,有些女孩對親密關係表現出膽怯和拒絕。
尤怡文提到,在瀏覽網絡論壇時,她發現了不少「撩妹」技術帖,將流行文化中霸道總裁的「壁咚」「腿咚」「摸頭殺」等招式應用在現實生活中。
「學校不教、爸媽不談的狀況下,青少年只好通過這樣的方式學習。這些缺乏正確性別平等教育的青少年,極有可能成為性騷擾或性霸凌的加害者卻不自知。」
撩妹套路,電視劇里看看就好。/《匹諾曹》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保護學生」
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起步於上世紀80年代末,由一些NGO倡議推動,其間經歷的許多社會悲劇,加速了性別平等教育制度化:
1996年,致力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女權運動者彭婉如遭性侵殺害,震驚社會,為回應社會對女性安全保障的要求,翌年出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要求各級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2000年,因性別特質長期遭受同學霸凌的中學生葉永志如廁時昏厥送醫不治,再次激發輿論對於性平教育的關切,2004年進一步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
現實里的地鐵公交,沒有浪漫。/《你的名字》
目前,台灣各級學校及政府都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針對不同年齡段學生製作教材,以手冊、影片等方式,結合生活案例,教導學生如何在尊重別人的前提下建立親密關係,並保護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台灣的校園裡,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講座層出不窮;電梯及女廁等隱匿的角落安裝防騷擾緊急求助按鈴;各級學校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在公共環境中,為防治性騷擾,城市公交車上不但張貼鼓勵女性遭遇性騷擾時要敢於求助的海報,並配備防性騷擾的求助口哨與警鈴,此外,還在火車站與汽車站設置全方位監控的夜間婦女候車專用區。
通過這次講座,尤怡文希望讓學生學會尊重別人、保護自己。會議結束前,她告訴來到現場的學生:「我們希望能提供一個訴說的地方。」如果有學生遇到性騷擾這類麻煩,可以聯繫她諮詢。「在有限的制度環境,我們能做的或許不多,但我們希望能讓學生知道,這裡有人願意聆聽陪伴。」尤怡文說。
余荼曾遇到一個色狼,後者坦言自己做了父親,每次在地鐵上性騷擾女性都很愧疚,也很害怕,但這個毛病就是改不掉。被警察抓住後,他的心裡反倒徹底踏實了。
按照要求,色狼去到派出所除了拍照、錄指紋,還要寫一份檢討書。在面對「如果是你的妻子、姐妹在公共場所被別人這樣對待,你怎麼想」的質問時,有的人會耍賴,說自己沒有家人;也有的人迷茫、彷徨,甚至向警察求助,反覆問——「你能幫幫我嗎?」
「親密關係中的不平等,特別是霸凌或控制的行為,很多時候是私人問題,但也必須有公權力的介入。」酈菁認為,面對性騷擾行為,要進行教育,要有懲戒機制:首先讓這些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有什麼問題,每個人該如何平等地看待各種關係;如果無法通過教育糾正,就要通過強制的公權力來解決,保證社會公平、公正,保證公民人格的平等。
沖繩電車站台的告示:「性騷擾是犯罪行為。」/Mk2010
「從社會公共層面上說,我們可以進行教育,通過媒體、學校或其他公共教育渠道進行。不光是教育受害的人、施暴的人,也要教育那些有問題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也教育公眾。」酈菁希望,通過性別教育,不僅幫助受害者,也挽救施害者。
幾次跟拍下來,余荼發現地鐵色狼的喜好各有不同:有人喜歡穿裙子的,有人喜歡穿牛仔褲的,有人專門選長頭髮的,有人喜歡瘦的,有人喜歡屁股大的。所以,是否會被盯上,並不完全是由穿衣打扮決定的。
獵狼小組的民警說,女生們該怎麼穿就怎麼穿,這個花花世界,大家要像花兒一樣,應該活得豐富多彩一些。至於違法者、犯罪嫌疑人,就交給警察來處理吧。
作者 | 衛瀟雨
原標題:《北京地鐵如何抓色狼》
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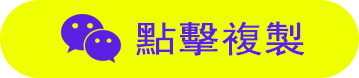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兩個人的感情往往都是當局者迷,找人開導一下就豁然開朗了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