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開朗基羅·梅里西·達·卡拉瓦喬於1571年下半年出生於意大利米蘭,他是一位極致自由灑脫的藝術家,一位跳脫常規的天才。
卡拉瓦喬是意大利北部一個村莊的名字,也是他們家族的來源,讀起來就像兩個連在一起的詞——明暗對比(chiaroscuro)和自吹自擂(braggadocio)。他小時候在米蘭和卡拉瓦喬村長大,據說也算出身於低階貴族。6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和祖父在同一天被瘟疫奪走了生命。大約13歲的時候,他成為當地畫家西蒙·彼得扎諾的學徒,也一定是在這個時期打下了一些基礎,如準備畫布,混合顏料,學習透視技法和繪畫比例等。他在靜物畫方面明顯天賦異稟,可能也是在和彼得扎諾學藝期間受到了萊昂納多·達芬奇以及喬爾喬內和提香等來自意大利北部的16世紀偉大畫家的影響。
卡拉瓦喬第一次去羅馬的時間很可能是在1592年,原因或許是他在米蘭捲入了一起警察受傷的事件(和他的大部分生平事跡一樣,此事的細節也模糊不清)。在這之前,他已經很久沒有出城了。
在羅馬,他很快就贏得了美譽,也背上了惡名。到1590年代中期,他的繪畫已經形成了我們所說的卡拉瓦喬式風格和主題——彈琴的人、玩紙牌的人和一群憂思的雌雄同體年輕人。顯赫的收藏家競相爭奪他的作品,包括兩位樞機主教斯皮昂·伯吉斯(Cardinal Scipione Borghese)和弗朗西斯科·馬里亞·德爾·蒙特(Cardinal Francesco Maria del Monte)。

卡拉瓦喬被成功沖昏了頭腦,或者說體內某種一直存在的因子被激活了。他的語言變得粗鄙不堪,酗酒問題惡化,經常打架鬥毆並多次被捕。
黃昏時分的羅馬。
1604年,32歲的卡拉瓦喬已經為羅馬的贊助人和教堂創造了一系列青史留名的傑作,比如康塔列里禮拜堂(Contarelli Chapel)收藏的《以馬忤斯的晚餐》和《召喚使徒馬太》,切拉西禮拜堂(Cerasi Chapel)的《聖保祿宗徒歸化》,另外還有《燔祭以撒》和《聖托馬斯的疑惑》等作品。這個時候,他也已經完成了《基督下葬》這件極具悲傷氣氛的作品,此畫即使以卡拉瓦喬的高超水準來看仍屬驚人成就。
而在個人行為方面,他依然魯莽且不顧後果。「有時候他可能會折斷自己的脖子或危及他人的生命。」喬瓦尼·巴廖內(Giovanni Baglione)說道,此人和卡拉瓦喬同時代,也是後者最初的傳記作家。
17世紀的作家喬萬尼·皮耶特羅·貝洛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曾經透露,「他以前在城裡經常佩劍出門,就像一個職業劍客一樣,似乎什麼事情都做,就是不畫畫。」有一次在酒館吃午餐的時候,卡拉瓦喬點了八顆洋薊。餐品端上來的時候,他詢問哪些用了黃油,哪些用了油,服務員建議他自己聞聞。生性多疑的卡拉瓦喬立馬覺得這是在侮辱他,於是一躍而起端起陶盤砸向服務員的臉。他接着一把抓起劍,服務員見狀倉皇而逃。
在拉各斯的童年時光,我會花好幾個小時專心研讀關於卡拉瓦喬作品的書籍。他的畫對讓我產生的感動又不安的感覺,不可能只是因為我熟悉他的作品。我那個時候喜歡的其他作品,比如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畫作,現在已經很少讓我心生波瀾,而卡拉瓦喬的迷人魅力倒是不減反增。
這也不可能只是因為他技藝高超,他的作品一般都有缺陷,存在構圖或前縮透視方面的問題。我認為原因在於,與前人相比,卡拉瓦喬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自我和感受。
卡拉瓦喬畫作的主題或源自《聖經》,或源自神話,但我們一刻也不會忘記這幅畫的作者是一個特定的人,一個有着特定情感和同情心的人。在卡拉瓦喬的畫中,我們可以找到創作者本人,可以感覺到他在呼喚我們。卡拉瓦喬同時代的人或許會對「多疑的托馬斯」這個聖經故事感興趣,可吸引我們的卻是托馬斯的不確定性,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體現了畫家自己的疑心。
但卡拉瓦喬身上的主觀性並不僅限於此,他獨特的主觀意識往往突出表現了生活中痛苦和不愉快的方面。他的畢生作品緊湊而嚴謹,充滿了威脅、誘惑和混沌。為什麼他會畫那麼多殉難和斬首的場景?我們希望生活中較少看到恐怖的一面,但它確實存在,我們有時也不得不面對它。卡拉瓦喬與索福克勒斯、塞繆爾·貝克特或托妮·莫里森等人有相同之處,但又有別於他們,他與我們一同前往現實中那些痛苦的地方。我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能夠感覺到他不只是為我們引路。我們意識到他其實就住在那裡,住在那些痛苦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的不安。
那不勒斯街邊。
1606年5月底,洋薊事件的兩年後,卡拉瓦喬在一場網球比賽中打賭輸給了一位名叫拉努奇奧·托馬索尼(Ranuccio Tomassoni)的男子。兩人發生了打鬥,隨後又有幾人參與其中。卡拉瓦喬在打鬥中頭部受傷,但他用劍刺死了這名男子。
在羅馬躲藏兩天後,他逃離了這座城市,先是到科隆納家族(the Colonna family)位於城外的莊園,後來又到了那不勒斯。他成了一名逃犯。
卡拉瓦喬的事業成熟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羅馬時期和謀殺托馬索尼後的時期,神奇的地方在於他在逃亡階段完成了很多事情。他的作品發生了改變,筆法變得鬆散,主題更加消極,但他依然高產並繼續受到贊助人青睞。他在那不勒斯、馬耳他以及西西里島的三個不同城市工作過,隨後又回到那不勒斯,接着在1610年動身前往羅馬,希望得到教皇赦免。他在回羅馬的途中喪命。
2016年夏天,我計劃去羅馬和米蘭工作。當時美國正在進行總統競選,報道鋪天蓋地,整個國家陷入了精神崩潰的狀態。唐納德·特朗普匪夷所思地獲得了候選人資格,並藉此突破重圍參與競選。此外,右翼運動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為了逃離戰爭和擺脫經濟困境,成千上萬的人死在了地中海。殘暴的ISIS組織發布的斬首視頻也已讓人屢見不鮮。我對那個夏天的記憶便是:厄運不止在即,它已經降臨了。(厄運降臨過,後來又演變過,而四年後的現在則是另一番罪惡。)
我知道自己在羅馬和米蘭的時候會去重溫卡拉瓦喬的畫作。至少他會告訴我關於厄運的真相,我也會在他身上找到某些藝術家能在黑暗時期給予我們的喘息機會。就在那時,我又冒出一個長久以來的想法:如果我繼續往南走,去卡拉瓦喬流亡過的每個地方呢?他在那些地方的作品很多都保留了下來,有些還是原地不動。這些地方包括那不勒斯、瓦萊塔、錫拉庫薩、墨西拿,或許還有巴勒莫。我越有這個想法,就越想付諸實踐。我並不是想來一趟豪華的夏日旅居體驗。
卡拉瓦喬的流亡之處都成為了移民危機的熱點地區,這並不完全是巧合,他當年也是因為這些地方都是港口才去的。港口能讓人去到一個地方,也能讓人逃離一個地方,陌生人在這裡也會讓人感覺不那麼陌生。兩大原因決定我踏上這段旅程:首先,我渴望感受到在博物館和教堂看到卡拉瓦喬畫作時的那種騷動情緒;其次,我想看看當時牆外的世界發生了什麼。
那不勒斯跳水的人。
六月底的時候,我從羅馬坐火車抵達那不勒斯。這是我第一次來這座城市,出租車司機一定也猜到了這一點。這位中年男子跟我解釋,從那不勒斯中央火車站到目的地的價格是固定的25歐元。當酒店的禮賓部跟我確認這趟車費不應該超過15歐元時,司機已經不見了。
那天晚上,在距離酒店半個街區的麥地那街(Via Medina)上,我經過一位睡在地上的婦女。一條小毯子蓋住了她的大部分身體,但雙腳卻露了出來,這讓我想起了卡拉瓦喬《聖母之死》畫中聖母瑪利亞那雙光禿禿的髒腳,這一形象最初曾讓一些藝術評論家大為惱火。第二天,那位婦女已經離開,但我看到另一位女性坐在同一個地方附近,用含糊不清的言語朝着路人大喊。或許連意大利人都無法聽懂她說了什麼。
那不勒斯是卡拉瓦喬流亡生涯開始和結束的地方。他第一次來是1606年晚些時候,第二次則是1609年,兩次都有重要委託在身。到了1606年10月,他已經收到無數邀約,並受到那不勒斯最高藝術圈的歡迎。他在那不勒斯完成的首批作品包括了為新成立的仁慈山小教堂(Pio Monte della Misericordia)慈善組織創作的《七善行》。卡拉瓦喬很快就交付了作品,也很快就收到了報酬。我們現在還能在位於市中心狹窄的法庭街(Via dei Tribunali)的教堂中,欣賞到這幅巨型畫作。
《七善行》是一幅複雜的作品,它試圖將七個不同的片段整合到一個垂直面中,與七宗罪形成寓意對比。這幅畫的複製品的畫面顯得擁擠不堪,但原畫在現實中的觀感卻不一樣,在八角形的小建築里看到這幅超過3.6米高的作品,着實令人嘆為觀止。
主角們從黑暗中浮現,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當觀眾把目光移到畫作的其他地方時,他們似乎又回到了黑暗中。這幅畫的右邊描繪了一則關於行善的古羅馬寓言:女兒哺乳救助身陷囹圄的年邁父親西蒙。她的身後有一具屍體被抬出(我們只能看到雙腳),寓意埋葬死者。前景則是一個赤裸身軀的乞丐,他躺在聖馬丁腳邊,此處寓意施衣予裸者。
《七善行》憑藉着堆疊的敘事方式和光線效果,為卡拉瓦喬之後的那不勒斯繪畫帶來轟動性影響。這對他來說已經形成了一種模式:不管住在哪座城市,他就像一道閃電一樣射出耀眼而短暫的光芒,一切因而變得不同。當我走出教堂步入法庭街時,《七善行》那洶湧澎湃的動感以及光與暗的鮮明界限,似乎延伸到了這條繁忙的街道上。
抵達那不勒斯當天,我看到一些年輕的非洲男子在中央火車站外售賣襯衫和帽子。那天下午,我從新堡(Castel Nuovo)走到蛋堡(Castel dell』Ovo),看着一些戲水的小男孩從堤道跳到了海灣中。有一位男子在城堡的入口處賣小飾品,他是塞內加爾人,有時候也會翻譯一些書籍。他精通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他告訴我,自己目前從事的項目與意大利的非洲人有關。我問他那不勒斯的非洲人在什麼地方,他說我興許能在加里波第廣場(Piazza Garibaldi)找到一些。不過他補充道,我晚上是不會想去那片社區的。
那一晚,我轉而選擇到西班牙人聚居區閒逛,卡拉瓦喬當年就住在這裡,並在此感受到了高雅文化結合低俗生活的迷人魅力。這一片街道狹窄,房屋高大,許多牆壁上都有塗鴉,感覺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喧鬧歡快的地方,帶着一種隱蔽而又輕鬆的氛圍,對於一個在逃的人來說正合適。當晚,這裡擠滿了居民、學生和遊客。在我吃飯的那家披薩店,服務員是一個快樂的年輕人,他的手臂上有一個紋身:我來過,我見過,我征服過。這當然是凱撒大帝的一個典故,但我後來發現,它也可能是當時復甦的意大利極右翼運動用來識別成員的標記,表達了他們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懷念。
隔天早上,我去了位於城市北部的卡波迪蒙特國家博物館(Museo di Capodimonte),這座建築曾是波旁王朝那不勒斯及西西里君主的宮殿。經過一排整齊排列的房間之後,我來到了卡拉瓦喬創作的《被鞭打的基督》畫前。畫中的基督以真實尺寸呈現,他站在一根圓柱前面,被三位攻擊者圍着,其中兩位拉着他,另一位屈身拿着鞭子。和往常一樣,卡拉瓦喬這次也描繪了一個故事,但又不止如此。他一般會通過不自然的陰影、簡化的背景和有限的調色板,讓情緒加劇宣洩,甚至超過了故事本身。這幅畫面充滿了殘忍與不公,讓我們不禁質問為何要折磨他人。
那不勒斯的卡波蒂蒙特國家博物館。
我於傍晚離開了博物館,走下卡波迪蒙特山,漫步在繁華的城市中,內心充滿了痛苦。我覺得有人正在門口和窗口注視着我。我開始想到卡拉瓦喬逃亡時無法理所應當地睡個好覺,但也發現此時此刻這座城裡的每一個人,他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朝不保夕的旅客:麥地那街上睡在門口的婦女,在蛋堡賣小飾品的男子,還有我在火車站看到的那些非洲年輕人。
我在那不勒斯欣賞到了卡拉瓦喬的兩幅晚期傑作,想看第三幅的時候卻發現已被外借,那幅《聖厄休拉的殉難》據說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我決定第二天去巴勒莫。我並沒有按照正確的順序旅行,卡拉瓦喬當年從那不勒斯去了馬耳他,然後又去了西西里島,最後回到那不勒斯。但直覺讓我把馬耳他放到了最後,讓這趟遙遠的夢想之旅在這一站告終。
回到酒店房間時,夜幕已降臨。我俯瞰那不勒斯這座城市,房屋在黑暗中緊密地挨着,燈光像一團螢火蟲一樣閃閃發光,一直蔓延到水邊,那裡停靠着渡輪和遊輪,遠處是幾乎完全處於黑暗中的那不勒斯灣、維蘇威火山、卡普里島和地中海。
聖洛倫佐小教堂坐落在巴勒莫的因馬科拉泰拉街上,周邊是雜亂的街道,狹窄而曲折,以至於我走到附近的時候還沒有看見教堂。在轉錯兩個彎之後,我終於找到了入口。
在教堂的主祭壇上,卡拉瓦喬的《聖方濟各、聖勞倫斯與耶穌誕生》曾經在這裡懸掛了幾個世紀。他可能是在1609年畫了這幅作品,但其相對保守的風格(構圖元素讓人想起他的早期作品《召喚使徒馬太》)加上文獻的缺失,讓人們對具體日期產生了懷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該作品創作於1610年以前,它一直被巴勒莫視為珍寶,直到1969年10月17日晚被不明人士從畫框中割走,從此下落不明。
大家現在一致認為,黑手黨很有可能參與了這起盜竊案,並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決定了這幅畫的最終命運。那麼最終命運如何?這一點眾說紛紜,有人說被廉價出售,有人說拿去餵豬,有人說被火燒毀,但沒有人確切知道。如今,在原來的位置上掛着一幅2009年委託別人製作的複製品,它根據原畫的照片繪製而成,但大膽的風格看起來根本不像卡拉瓦喬的真跡。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紙質旅遊宣傳冊上讓遊客把目光投向別處,去欣賞「弗朗西斯科·卡曼利諾(Francesco Camanlino)和阿洛伊西奧·米拉(Alojsio Mira)兩位藝術家在1716年設計的迷人大理石地板」。
但我的朝聖之旅並不是來看大理石地板。卡拉瓦喬的作品很少,學者們一致認為其數量在80件左右,所以那些缺失之作就像傷疤一樣,包括17世紀的作家提到的一些未能倖存或未被鑑定的作品,1945年燒毀於柏林的三幅,以及縈繞在巴勒莫小教堂的這一幅。
那個夏天,意大利的生活並不安穩,而西西里島有其獨特的困難之處。例如,我不太確定自己看到的很多帶有「極端」(ultras)一詞的塗鴉是指狂熱的足球迷還是右翼政治暴徒,或是兩者的結合。
有一天下午,我頂着炎熱的天氣去逛巴拉羅市場(Ballarò market),攤位上花里胡哨地擺着農產品和廉價商品。我返回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這座城市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市場已經收攤,街道上幾乎一片寂靜。當時有傳聞稱,巴勒莫的一些尼日利亞人與黑手黨發生了衝突,說他們參與賣淫,然後既遭受了可怕的暴行,同時又是施暴的一方,還有一些持刀傷人事件發生。我在逛巴拉羅市場的時候並沒有看到這些行為,但氣氛很緊張,我清楚自己不想繼續逗留。
第二天早上,我從巴勒莫乘火車沿着西西里海岸前進,途經切法盧(Cefalù)、卡普多蘭多(Capo d』Orlando)、焦約薩馬雷阿(Gioiosa Marea)和巴切洛納(Barcellona)這些陌生城鎮,最後來到了墨西拿。我在這個過程中明白了兩件事,一是我再也無法將卡拉瓦喬流亡歲月的探索之旅與當前在意大利的所見所聞分割開,我們看到了同一片大海,也都感受到了危機;二是在那不勒斯無緣欣賞《聖厄休拉的殉難》,隨後又在巴勒莫看到《耶穌誕生》的複製品並感受到意料之中的失望後,我現在已經完全準備好面對卡拉瓦喬的其他偉大真跡。我在墨西拿火車站坐上一輛出租車,司機問我:「你是足球運動員?」我笑了起來。的確,一個前往酒店的非洲年輕人,除了球員還能是什麼呢?「不,我來看卡拉瓦喬的畫。」「啊,卡拉瓦喬,」他不相信地說道,「卡拉瓦喬,很好。」
在墨西拿箱子裡的足球宣傳畫。
我坐在房間中央的一張長凳上,兩幅畫形成了一個直角。我夾在這兩幅巨作之間,內心充滿敬畏,喘不過氣來。欣賞古畫這個行為本身就能帶來奇特的感覺,它經常與階級身份或社會抱負聯繫在一起,就像漫步於白人祖先身旁,時而愉快,時而不快。
它通常是一種美妙的體驗,讓觀眾有福氣欣賞到一位陌生人的巧思妙解。但在少數時候,可能會發生更為美好的事情:來自遙遠國度的人幾百年前所畫的一幅畫鋪開在你面前,畫布中沉澱着這位藝術家的細緻觀察和動盪經歷,然後它從遙遠的過去躍出來召喚着你,召喚你關注當下,讓你警覺而又感到安慰,這讓你困惑不已。通過體驗這種遠超語言把握的感覺,這種你希望與之共存的感覺,它讓你意識到了自身。
《拉撒路的復活》大約畫於1609年,畫面上方被黑暗所占據,而下方則像是在聚光燈下上演復活的場景。拉撒路的身體斜在畫面中央,蒼白而泛綠,在生死之間拉鋸着。一位男子扶着拉撒路的身體,他的姐姐們則在右方哀悼。左邊是基督的形象,頭部背着光,他伸出右臂在喚回死者的生命。金色的光芒灑在畫面中的手上、臉上、手臂上和腿上。
《約翰福音》中講述的拉撒路的故事一直讓我深受感動,故事的基本框架清晰,讓人產生共鳴:有人去世了,心碎的家人請求挽回生命。在拉撒路的故事中,其家人的悲痛心情讓基督動容,於是他干涉事物的自然秩序,破例讓其死而復生。這個故事樹立了一個得到上天偏愛的典範,而我們在最受傷最脆弱的時候都希望能有此幸。卡拉瓦喬通過物質現實來明確這一場景:旁觀者困惑的表情、姐姐們沮喪的面孔、拉撒路壞死的身體,以及基督的超自然權威。
相比之下,《牧羊人的朝拜》所演繹的故事則要溫和許多。基督出生時的馬廄可以怎麼表現呢?許多藝術家囿於故事的童話包袱,但卡拉瓦喬的雙手給這個故事重新注入活力。和往常一樣,關鍵就在於他對現實主義的信任:展示事物的樣子,感覺自然會隨之而來。這幅畫以棕土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央胎盤般的紅色十分醒目,那是聖母和其中一位牧羊人所穿的長袍。卡拉瓦喬並沒有描繪一個溫馨的家庭場景,而是刻畫出粗糙和困窘。為什麼一個新生兒和他的母親要待在這樣一個骯髒惡劣的地方?這難道是在難民營里?這些人為什麼沒有家呢?
卡拉瓦喬1607年離開了那不勒斯,1608年晚些時候去到西西里島,在錫拉庫薩、墨西拿,或許還有巴勒莫這幾個地方接受委託進行創作。
不過中間的那一年多時間裡,他待在更南邊的馬耳他。他當時不得不離開那不勒斯,原因不明。雖然卡拉瓦喬逃到了馬耳他,但他依然本性難改,又因為犯罪而不得不逃亡他處。當他離開西西里島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又得倉促行事,這一次是因為他擔心自己的性命。他從西西里島回到那不勒斯,然後又啟程前往羅馬。
在生命中這段錯綜複雜的最後年月,他十分高產,但又疲於奔命,無家可歸。不難想象他在畫《牧羊人的朝拜》時,內心或許對這個神聖的家庭產生深深的共情。畢竟,他們面對的是人類最簡單也最複雜的需求——一個安全體面的容身之處。
在墨西拿的酒店裡,我讀了那天早上《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關於一年多以前一艘載有700人的船沉沒的報道。那艘船現在已經被意大利海岸警衛隊打撈上來,正從海上運往西西里島的奧古斯塔港(Augusta)。我決定前往這個港口觀看船隻停泊。
在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離開了墨西拿,一路沿着海岸往南行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可以在右側看到埃特納火山煙霧繚繞的山峰,中途還路過了陶爾米納和卡塔尼亞。我們抵達奧古斯塔城鎮的時候,天色明亮,人煙稀少。我們在一家咖啡館裡吃午飯,但打探不到任何關於那艘船的信息。於是我們繼續南下,經過錫拉庫薩後一路去到島的最南端,到達旅遊勝地波扎洛(Pozzallo)。我們穿過城鎮的時候,交通十分擁擠。一輛靈車駛過,後面跟着一大幫步行的人。
在波扎洛的海灘上,我們和意大利及美國的朋友會合,然後開車去到港口區,那裡通常停靠着渡輪和集裝箱船。大門開着,但窗口沒有人,地面上也沒有其他人。在港口區後面,碼頭和公路之間,大約離我們50米遠的地方有一個用柵欄圍起來的泊船處,裡面停靠着八艘大型木船。它們有藍色、白色和紅色,互相停靠得很近並朝一邊傾斜着,有幾艘還靠在了一起。
我把同伴們拋在身後,自己朝着這些船走去。甲板上放着橙色的救生衣,其中有一些掉了出來。等我走到船邊的時候,它們所散發出來的強烈氣味已經變成一股惡臭。這些船是從海里拖上來的,似乎沒人打算清理一下。它們不僅掛着大量骯髒的救生衣,還有塑料瓶、鞋子、襯衫以及人類近距離生活多日所留下的髒東西。
停靠在波扎洛港的移民船。
如果是這些船的話,我無從得知是哪艘把乘客傾倒在地中海里,哪幾艘被歐洲當局攔截,哪幾艘又把驚恐的旅客安全帶回岸上。我帶着筆記本走在它們中間,把自己所看到的記錄在本子上。我觀察着這些細節,不知道要怎樣把它們都寫下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我自己也大吃一驚:我突然跪倒在地,開始抽泣起來。我的胸膛跳動着,眼淚流了出來。在這些散發着強烈人體氣味的船舶之間,我雙手抱頭,被突如其來的悲痛之情所震驚。
我鎮定下來之後,爬上了其中一艘船,此刻已不再被惡臭所困擾,只想待在那裡想象那些看不見的船員有多麼絕望。過了一會,我又回到朋友身邊。我們駕車離開波扎洛,回到了奧古斯塔。這是一個省級港口,隨處可見起重機、船舶和集裝箱,比波扎洛那邊更繁忙,規模也更大。有一片區域被柵欄圍了起來,裡面設置了一些帳篷,住在裡面的人有的已經在過去幾周或幾天內被接走,有的則還在等待程序處理然後轉移到其他城市。有人告訴我們,那艘本來應該過來的大船當晚不會停靠在這裡。
不過,當天已經有一小部分移民抵達,一名警官允許我和其中兩人交流。我被帶到一個燈火通明的房間裡。這兩名男子都是孟加拉國人,都很年輕,大概20多歲,看上去一臉茫然。他們都得到了乾淨的衣服,其中一人穿着帶紐扣的格子襯衫,另一人穿着運動T恤,腳上都穿着塑料洞洞鞋。他們大概在說孟加拉語,旁邊一名能說一口流利烏爾都語的巴基斯坦男子在擔任翻譯。他大概知道兩人在說些什麼,我猜可能是因為兩人也懂一些印地語,而印地語和烏爾都語還是有不少相似之處的。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這位口譯的意大利語很流利,但英語說得結結巴巴的。所以,我們花了一些功夫讓他理解我的問題,又花了一些功夫讓兩名孟加拉國男子理解這名口譯的轉述。當他們終於聽明白問題並作出回答之後,同樣需要經過一番折騰才能傳達給我。
兩人的名字都是默罕默德,其中一人體型比較大。他們是被一艘來自利比亞的船救上來的,之前已經在那裡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為什麼離開孟加拉國呢?他們的回答是為了找工作。那利比亞的情況如何?大默罕默德搖了搖頭,表示情況非常糟糕。利比亞人很殘忍,他們必須離開那裡,但上船需要花不少錢。那這趟旅途如何?這次又是大默罕默德回答,他告訴我人販子騙了他們這些乘客,之前本來說6個小時就可以到意大利,但在海上漂了幾乎一整天后才被意大利的船接走。
我問他們想做什麼,這一次是小默罕默德開口說話。他說兩人想要在歐洲自由地工作,另一個人點了點頭。他們的疲憊顯而易見,畢竟剛從海上的磨難中倖存下來。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地方:他們活了下來,但是其他人卻死了。事情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這是運氣問題,他們似乎也因此困惑不已。
移民船上留下的生活痕跡。
我們被告知當晚還會有另一艘船停靠在奧古斯塔,不過是在另一個小一點的港口,過去的話需要幾分鐘車程。我們又得到消息說,之前期待的那艘大船已經被當局禁止靠岸了,不過船上有少量乘客被帶上岸接受緊急醫療護理。我們於是去到那個港口,大約半個小時後,的確有一艘被蓋住的小船過來。碼頭上還有其他媒體人士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得到允許可以目睹船隻靠岸,但不得靠近或拍照。警察在這個區域巡邏,大概有六名醫護人員全身穿着白色的防護裝備,戴着口罩登上了船。他們很快就抬下來一個虛弱的人,把他放到擔架上,然後推上救護車。一位意大利記者猜測這個人來自厄立特里亞。
不久之後,這些醫護人員領着一對黑人夫婦從船上下來,接着是第二對。兩位女性都懷有身孕。四個人都被扶着下船上岸,然後帶到在碼頭邊等候的救護車上。我也跟着去到救護車旁邊。其中一位男子坐在車門旁邊,我問他從哪裡來。「尼日利亞,」他說道。我覺得自己可能僭越了,但同時也認為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不會聽到太多溫柔的話語,於是我說了一句「歡迎」,然後又補了一句「願神與你同在」。還沒等到男子回應,一位警察就關上了救護車門,並揮手示意我離開。
錫拉庫薩是用一種蜜黃色的石頭建成的,同樣的石頭也被用來建造簡陋的住宅,還有城市守護神聖露西的大教堂。關於她的傳說具有典型的基督教女性聖徒特徵:宣誓貞潔,奉獻上帝,蔑視世俗權威(錫拉庫薩總督),隨後是可怕的處決。露西的傳說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說她的眼睛在處決前被挖了出來。聖露西是盲人的守護神,她在大教堂頂部的雕像舉着一個盛放自己眼睛的盤子。
錫拉庫薩的一個人幫我聯繫到了一位來自岡比亞的年輕人,他在大概個月前從利比亞乘船來到這裡。這個年輕人我們暫且叫他小D。他以未成年人的身份進行了註冊,但承認自己已經成年,我估計他20歲左右。他和其他未成年人一起被安置在一個團體之家。小D有一張黝黑而聰穎的臉,舉止親切,讓我想起了我的表(堂)弟們。他似乎很開心能和別人說英語,聽到我也是尼日利亞人的時候就更高興了。「我喜歡尼日利亞的音樂,」他說道,「我只聽這個。」我問他為什麼要遷到這裡來。他說自己的父親是一位不入流的政客,然後和岡比亞時任總統葉海亞·賈梅發生了衝突。「我的父親被迫流亡達喀爾,家裡處境非常困難。所以我是為了母親,為了姐妹們。」不過,他為什麼不一起去達喀爾呢?「我和父親的關係不是很好。」小D的父親隨後去世,情況就更加讓人絕望。他去利比亞找工作,並設法寄了一點錢回家。他後來決定付錢給人販子過來歐洲。他並沒有把這個決定告訴家人。
「你不怕死嗎?」
「有點怕,」他說道,「但利比亞變得很亂,我必須離開。」
年輕的移民小D從利比亞乘船來到錫拉庫薩。
這和那兩位穆罕默德的情況本質上是一樣的。「路上的情況是不是和你擔心的一樣糟糕?」「更糟糕,」他說道。人販子給了其中一位乘客一台收音機,於是他們便隨意地任命這個人為「船長」。這個人接到的指示是在一段時間之後想辦法聯繫上一艘來自意大利的船。經過狂亂的數小時後,這個計策奏效了,這些移民被接送到了西西里島。小D直到成功上岸,才告訴家人自己來了歐洲。他說意大利人對他很好,他還住在收容未成年人的地方,在那裡相對自由一些。不過,他並沒有多少錢,也沒有僱傭證書。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他現在渴望離開錫拉庫薩,到一個更大的城市去。
他隨後問我為什麼來錫拉庫薩。我告訴他,自己是來看卡拉瓦喬的畫。我指着大教堂廣場,問他要不要陪我一起去。他說沒什麼不可以的。我們一起走進巴提亞的聖露琪亞大教堂(Santa Lucia alla Badia)的時候,他說道:「你知道麼,我每天都來這裡,在廣場附近轉悠,但從來沒有進過任何一間教堂。我指的是自己這輩子都沒有進過教堂,我不知道教堂裡面長什麼樣。」小D從小就是穆斯林。他似乎很驚訝自己可以直接走進來,沒有人質疑他為什麼在這裡,也沒有人在門口攔着他。我們走到了聖壇裝飾畫前面。
移民小D。
這幅《埋葬聖露西》十分巨大,有3米寬,高度超過4米。它的保養狀況很糟糕,顏料表面有磨損,畫本身也有大面積損壞,但並沒有削弱這幅作品的表現效果。
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這幅畫在物質上的脆弱有助於人們把注意力放到其悲傷情緒上。已經死去的聖露西張開手躺在地上,脖子上有一道切口,眼睛緊閉着。一群人聚集在屍體後面。畫面的前景是兩位壯漢在挖土,但這片「土地」與深棕色的主色調相融,看上去仿佛是時間正在掩埋這幅畫作。
黑暗從各個方面侵蝕着主角。小D看着這幅畫的時候,我想告訴他卡拉瓦喬彼時已經有些偏執,四處奔波的他會佩劍入睡,但我沒有說出來。在外面的時候,小D的眼神充滿了驚訝,這份驚訝不僅是對卡拉瓦喬,也是對我。我這個陌生的西非同胞不知從哪裡冒出來,問着一些怪異的問題。
從空中來看,馬耳他最大的島嶼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塊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型軟木板。一片褐色的平地在水面上延伸開來,周圍是令人眩暈的懸崖。從機場出來的路上,出租車司機主動說道:「馬耳他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我們無法養活這些難民。我們是一個小島,不是一個大國。」馬耳他的出名之處在於保存完好的房屋和教堂,莊嚴的聖天使堡,還有耶路撒冷、羅得島及馬耳他聖約翰主權軍事醫院騎士團廣泛深遠的影響。這個激進的基督教組織又稱馬耳他騎士團,正是其提供的贊助吸引了卡拉瓦喬在1607年7月來到馬耳他。
卡拉瓦喬在馬耳他住了一年出頭的時間,在那段時間裡為騎士團畫了少量的畫。這個組織的主保聖人是施洗者聖約翰。卡拉瓦喬為騎士團首領阿洛夫·德·魏格納克特(Alof de Wignacourt)畫的那幅嚴厲而充滿責任感的肖像,正懸掛在盧浮宮裡。魏格納克特的另一幅肖像畫可能已經遺失。身背托馬索尼命案的卡拉瓦喬可能是想用這些畫來討好魏格納克特,讓自己得到對方青睞,如此一來這位首領就會授予自己爵士頭銜,從而增加自己被教皇赦免的機會。這座島上還有兩幅卡拉瓦喬時代的重要畫作。第一幅是《聖傑羅姆寫作中》,第二幅則是《被斬首的施洗者聖約翰》,我正是因為後者才來到馬耳他。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便已知道這幅畫,當時我還不知道馬耳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
馬耳他人口最多的地方是首都瓦萊塔附近密集的城鎮。我住在其中一座叫斯利馬(Sliema)的城鎮,在水邊就餐,在相對安靜的街道上散步閒逛。直到第三天,我才鼓起勇氣去瓦萊塔的聖約翰聯合大教堂(Co-Cathedral of St. John)。之所以叫聯合大教堂,是因為馬耳他以前的首都姆迪那(Mdina)已經有一座教堂。這座聯合大教堂金碧輝煌,迴蕩着遊客的低聲細語。
不過如果你按照指示走,穿過後面的一扇小門,就可以進入一個安靜的小房間,這裡就是小教堂。正前方便是《被斬首的施洗者聖約翰》,但只有繞過一堵固定的隔牆才能看到。如果你這麼做的話,就會走進一個可怕的場景,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東西。
畫中描繪的7個人感覺就像生活在真實空間中的真實人物,在黑暗的背景下顯得矮小。這幅畫的光線、畫幅(甚至大過《埋葬聖露西》)、懸掛高度以及明暗分布,都讓人感覺是在圍觀一場真實事件:兩名囚犯看着處決的過程,一位女僕拿着金盤子,一位老婦人,一位施令的男子,一位拿着刀的劊子手,還有聖約翰本人,他倒在地板上,脖子鮮血直流。卡拉瓦喬在下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就我們知道的情況來看,這是他唯一一次這麼做。他從這攤血液中劃出了一道紅線。
我前兩個星期從卡拉瓦喬畫作中感受到的邪惡力量——《朱迪絲斬首霍洛芬》《聖馬太受難》《大衛手提戈利亞的頭》《被鞭打的基督》,這些殺氣騰騰的能量現在似乎壓縮成了一個噩夢的形象,一個瞄準犯罪現場的監控攝像頭,一場虐殺電影。
《被斬首的施洗者聖約翰》這幅畫很難融入我對繪畫本身的理解。一年多以後,我看了兩段2017年於利比亞拍攝的短片,才找到方法來消化在馬耳他的所見所聞。第一個片段是關於奴隸市場販賣人口,拍攝者不詳。第二個片段是CNN的記者前往的黎波里(Tripoli)郊區求證此事的報道。那些被販賣的人是來自尼日爾的移民,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黑夜中靠着一堵光禿禿的牆站着,就像卡拉瓦喬畫中那個荒涼的庭院。片段中光線不佳,能見度低,但還是能發現這個市場生意興隆,交易迅速,有人開價,看不見的買家競標,然後就結束了。在那些片段中,我看到生命完全變了樣,從生變成了死,正如我在卡拉瓦喬作品中看到的那樣。事情不應該是這樣子,也不應該被呈現給世人。
卡拉瓦喬的這幅畫給東道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08年7月14日,他在完成這幅畫後不久,就被授予聖約翰騎士團騎士稱號。阿洛夫·德·魏格納克特公開將他比作古代最偉大的畫家阿佩萊斯(Apelles)。卡拉瓦喬還得到了一根金鍊,而且根據喬萬尼·貝洛里的說法,魏格納克特還「賜給他兩名奴隸」。
當時,馬耳他騎士和奧斯曼帝國互相仇恨對方,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有許多被奴役的基督徒,而馬耳他的大多數奴隸都是穆斯林。我們並不清楚卡拉瓦喬兩名奴隸的身份,但許多在馬耳他國內工作的奴隸都來自波努(Bornu),它涵蓋了如今尼日利亞和乍得的部分地區。
這一殘忍的享受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卡拉瓦喬在八月底的時候又捲入了一起暴力糾紛。高級騎士喬萬尼·羅多蒙特·羅埃羅(Giovanni Rodomonte Roero)有一天晚上被襲傷,卡拉瓦喬和其他5人與此有牽連。他在聖天使堡被關押了幾個星期。不過,卡拉瓦喬不知怎的避開了囚禁,用繩子從城堡中滑了下來。他找到一位船夫,可能也賄賂了對方,然後徑直前往西西里島。就這樣,他來到錫拉庫薩、墨西拿和巴勒莫,那幾個月裡面完成的傑作讓他曝光度大增。
後來,他覺得自己在西西里島受到了生命威脅,或許是怕馬耳他騎士找上門來,他回到了那不勒斯,在這座熟悉的城市裡繼續高效創作。他以為自己在這裡會很安全,但是他錯了。1609年10月,卡拉瓦喬從酒館出來以後被一群人圍住。他們圍毆這位畫家,還砍傷了他的臉。根據猜測,他在這次遇襲後變得腿腳不便,也喪失了部分視力。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康復。從遭遇襲擊到最後離世的這9個月時間裡,他只創作了幾幅畫作,最後兩幅據說是《聖彼得的否認》和《聖厄休拉的殉難》。
那不勒斯之旅不到一年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就借到了《聖厄休拉的殉難》。這樣一來,我就可以並排欣賞到它和《聖彼得的否認》兩幅畫,因為後者正是大都會博物館的藏品。因為我們知道卡拉瓦喬不久之後便去世,所以會情不自禁地透過一種晚期風格的視角來欣賞這些作品,它們既表現了這位藝術家非凡的技巧,也流露出他的倉促感。這些畫兼具巨大的經濟價值和心理深度。聖彼得眼神中流露的恐懼,還有聖厄休拉臉上的悲痛,它們是否體現出一位知道自己生命即將結束的人的洞察力?我們很容易會有這樣的想法。不過,卡拉瓦喬當時希望的是從上一年的傷病中恢復過來,也希望得到教皇的赦免。雖然已經完成了大量巨作,但他當時才38歲,一定覺得一切才剛開始。他並不是像施洗者聖約翰那樣由生到死,而是像拉撒路那樣由死到生。所以他會有想法,有希望。
1610年夏天,卡拉瓦喬接到消息,在先前的贊助人斯皮昂·伯吉斯樞機主教的幫忙下,羅馬那邊正在為他安排赦免事宜。七月中旬,他帶上三幅畫打算送給這位樞機主教,然後乘坐一艘小帆船離開那不勒斯。一個星期後,他來到羅馬以西30公里的海濱要塞帕洛(Palo)。他大概打算從那裡前往羅馬,不過計劃泡湯了。卡拉瓦喬下船後便和要塞的軍官扭打起來,最後被逮捕。小帆船拋下他繼續航行,不過他的畫還在船上。它朝北駛向托斯卡納海岸,到達埃爾科萊港(Porto Ercole),或許有乘客要在那裡下船。卡拉瓦喬幾天後被釋放,他朝着埃爾科萊港的方向趕了一天的陸路。一到那裡,他就累得癱倒在地。小帆船大約在同一時間到達。
2016年7月時,我曾前往埃爾科萊港,當時天氣炎熱。我從羅馬乘火車出發,大約30分鐘後經過帕洛,一個半小時後抵達奧爾貝泰洛(Orbetello)和蒙特阿金塔里奧(Monte Argentario)。我可以理解,1610年7月趕這麼一趟旅程的話可能會患上熱病。我住在奧爾貝泰洛,第二天早上乘出租車出發。車子穿過一片土地,遠處是蒙特阿金塔里奧的一處海角,南邊就是埃爾科萊港。我在岩灘上的一家咖啡館裡吃早餐,旁邊坐着4位遊客,其中2位從口音上判斷應該是美國人。年紀較大的那位美國人說道:「這個人也許會贏得選舉,他可以結束這一切。政治正確太瘋狂了,你甚至不能再讚美任何人,他們會覺得這是性騷擾。」他滔滔不絕地說着,一副希望被別人聽見的樣子。他還抱怨了前妻,其他3位同伴同情地點了點頭。
卡拉瓦喬從未畫過大海,我曾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搜尋海景卻徒勞無功,其他任何一種景色也很罕見。我們只能談談他留下的這些作品,而在這些作品當中,你會發現沒有波濤,沒有海浪,沒有平靜的海洋,沒有海難,沒有海灘,沒有海上落日。然而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卻描繪了一張海圖,上面的停靠港都是名副其實的港口,也是希望的港灣;而埃爾科萊港則是意料之外的一站,更是最後一站。他被埋葬在那裡的某個地方,也許在海灘上,也許在當地教堂里。但他真正的主體可以說是在其他地方,他繪畫成就的主體,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幾十個地方,這些地方的牆上都會有一張標籤寫着「1610年死於埃爾科萊港」。
他是殺人犯,是奴隸主,是一個令人恐懼和討厭的人。但我研究卡拉瓦喬,不是為了了解人類有多好,當然也不是因為他這個人有多好。正正相反,我是希望從他身上了解某種平時難以忍受的知識。這位藝術家描繪了果實成熟後開始腐爛的時刻,刻畫了肉體最精緻性感和最殘缺受損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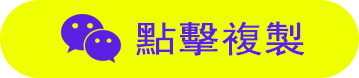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最近了解了一下,是我朋友給我推薦的,很靠譜,推薦大家情感有問題的可以嘗試一下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