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時代開放和社會變遷,性少數群體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然而,在公共討論與學術研究中,男同性戀被予以相對較多的關注,而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都仍處於邊緣的地位。
自 5 月 17 日「國際不再恐同日」以來,「偶爾治癒」相繼推出了老年男同性戀、老年女同性戀的稿件,試圖展示不同群體與個體的生存圖景和面臨的困境。
今天的這篇稿件,是一個中年拉拉走進異性婚姻,又從其中出走的故事。在當下主流的敘事語境中,她不是一個完美的「同性戀形象」。
但通過她的經歷,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在否定女性作為性主體的主流文化中,女同性戀們是如何周旋於自身非主流的性與性別,在「生兒育女」、家庭和睦、傳統孝道的強勢主流敘事裡,她們又是如何夾縫求生的。

這群中年女人的歡樂時光,是從周五下午六點半開始的。
呼和浩特的夏日傍晚,暑氣未褪,頂着曬得紅撲撲的臉蛋,女人們翩然落座,其中一對十指交纏,旁邊的人對視一笑,習以為常。
點煙、倒酒、寒暄。因為身體原因,聚會的發起者波樂,已戒酒三年。原本能拿一斤 50 多度白酒「潤潤喉嚨」的女人,拿起一杯芒果汁開場。
「那個誰呢?」「孩子高三,放學晚,她伺候過飯再騎車過來。」
酒過三巡,遲到的女人披着燙卷的長髮,穿着牛仔背帶裙撲進房間,親熱地抱住波樂的胳膊,「哎呀我來晚了」,門在身後闔上。
這扇門好像一道分界線。門外,她們是誰的女兒、妻子、母親,「完美」演繹各自的角色;門裡,她們屬於自己,嬉笑、大哭,親吻女友的臉頰,講私密的情話。
常聚一起的八個女人,都是「拉拉」(女同性戀別稱)。52 歲的波樂是她們中,唯一從異性婚姻離開,並跟女兒「出櫃」的人。
年輕時的波樂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如今的波樂已經不再遮掩自己的身份。手機殼印着凱特 · 布蘭切特和魯妮· 瑪拉精緻的側臉,是電影「卡羅爾」的劇照,講的是兩個女人的愛情故事。
「她是我們的光」,聚會上,有人偏過頭悄悄說,語帶艷羨。波樂做出的許多選擇,是一些人想嘗試但永遠不敢的。
「『出櫃』需要承受太大的風險」,聚會中,一位被卡在異性婚姻中的拉拉解釋,結婚生子後,她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原來是這樣的人」,但她沒有波樂那樣離開婚姻的勇氣。
但其實,波樂的「瀟灑」是有代價的。
她形容,自己原本是一棵自由生長的樹,但被社會規範、主流觀念強加了許多橫生的枝杈。她想活下去,就要砍掉了那些枝杈,很痛。
「但砍掉,就又是一棵自由自在的樹了」。
這是一種「宿命」
波樂出生在內蒙中部的一個城市,父親是蒙漢翻譯。1968 年,她出生時,因為捲入風波,父親關押,母親白天被隔離,9 歲的姐姐和 6 歲的哥哥帶着剛出生的波樂,生活了半年。
從小到大,父母兄姐都不會束縛波樂的天性,她沒玩過洋娃娃,也沒人跟她說,「你是一個女孩,你應該玩洋娃娃」。她喜歡短頭髮,穿褲子,大院的人嘲笑她,「不像個女孩」,她不服氣,「憑什麼這麼分,說什麼男孩才能做女孩才能做,我這樣好看,跑起來方便,我就這麼打扮」。
波樂五六歲時,父親被下放到達茂旗電影院做放映員,一家五口就住在影院裡,波樂對女性審美的啟蒙、對電影的熱愛都始於此。她至今還數得出上官雲珠、張瑜拍過的電影,那些富有韻味的眉眼,至今還在她記憶深處發光。
念書時,同學們嬉笑打趣,總會問「你喜歡誰」,大家都默認指的是異性。波樂也被問到這個問題,她想了想,覺得自己好像「也應該有喜歡的男生」,她選擇了自己的同桌,對方完全符合那個年代她從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習得的異性愛人的想象,高大正氣,濃眉方臉,「有點像陳寶國」。
但同時,波樂朦朧地察覺到自己對女性的好感,想親近的念頭總會躥出來。
初中,波樂和同一宿舍的女生打鬧,有了身體接觸,「好像打開了一個開關」,她感覺有些戰慄。對方似乎也有些察覺,靜默了片刻,兩人迅速分開,再也不提。
女孩間的親昵,在每一個年代都不會被視為洪水猛獸,要好的女生會牽手、摟抱,甚至親吻。不被過度關注,客觀上給拉拉群體提供了一個呼吸的空間。
1987 年,波樂進了呼和浩特一家報社,在圖書室工作。上個世紀 80 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圖書室里的波樂,再一次接受了洗禮。
她讀波伏娃的「第二性」、讀「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挪威的森林」,漸漸了解到,有個詞叫「同性戀」。後來,她讀「港台文學選刊」,讀邱妙津、劉索拉、陳染和曹麗娟,在作者的筆下,女性的自我和欲望被展示得淋漓盡致,張力十足。
波樂的書架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兩年後,在滑冰場上,波樂認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女人」,她們成為了一生的摯友,「第一眼看見她,像燕子一樣飛過,我就想着,好想認識她」。
波樂的相冊里有這個女人,黑白照片上,她眉眼姣好,齊肩的直發,站在山頂抬頭看着遠方,精神氣十足。某種程度上,這個女人是年輕波樂的「精神偶像」,她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公開交女朋友,大膽放肆,一生未婚。
年輕時的波樂並不能那般灑脫,她試圖抵禦過內心真切的渴望,如同年少時和室友的那次身體接觸,戰慄過後,迅速躲開。
那時候,波樂見過的,那些與同性戀愛的女生們,大都選擇結束愛情,滑進異性婚姻,完成自己「身為女性的義務」,把自己變成符合世俗意義規範的「妻子」和「母親」。
「像是一種宿命」。
婚姻是「必經之地」
工作後,儘管家人沒有催婚,但波樂能隱隱察覺一種無形的壓力,來自更大的世界。
「好像你在走一段路,大家都會默認,你必須過這一段橋或這一條路,才能達到你要去的地方,這是你成長的必經之地。也是社會給你的一種期許,如果想運行好你的角色,那你肯定得先完成這個任務。」
為「完成任務」,符合大多人對女性的「角色期望」,波樂接受了相親。「我覺得好像走進婚姻,就是對我爸媽的一種回報,這好像是我唯一能做的,告訴他們,嘿,不用擔心,我長大了,作為父母,你們的任務完成了」。
許多年後,波樂承認,那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波樂年輕時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她相過三四次親,直到遇見她認為可以走進婚姻里的人。這段婚姻始於 1995 年,一共維繫了 14 年。對於另一半,她一直用「孩子的父親」這樣的稱呼,而不是「我的前夫」。
對方是一個工會幹部,漢族,跟着爺爺奶奶長大。波樂欣賞他,這個人寫得一手好字,做飯好吃,喜愛唱歌和運動。如果拋去情感的牽絆,兩個人是絕好的玩伴和生活拍檔。
然而,違背內心意願,強行讓自己符合社會主流的角色期待選擇,願望與現實的錯位,讓這段婚姻註定是一幕彼此傷害的悲劇。
婚後兩個人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他們住在波樂姐姐的一套房子裡,各自財政獨立,大多數情況下,波樂承擔了家裡大部分開銷。
她形容這段有距離感的關係,「我不需要你的東西,不要求你做什麼,儘量不欠你任何東西」。這種距離感甚至體現在兩個人的照片中,為數不多的合影里,他們並排坐着,隔着兩拳以上的距離。
婚後,生育是必須面臨的問題,波樂對此本能地抗拒,甚至有過一次流產,「有孩子會讓婚姻和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複雜」。但婚後一年,對丈夫始終懷抱歉疚的波樂,決定生一個孩子,這是她給丈夫的交待。
孩子在肚子裡很體貼,有時安靜得甚至讓波樂擔心她是否安好。但波樂仍覺得痛苦,整個孕期只長了 10 斤體重。
「我不知道自己這個決定會帶來什麼結果,只覺得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
女兒出生後,波樂記得,丈夫還親手縫了被子和衣服。給孩子洗澡,都是「一隻手端着洗」,孩子睡覺都生怕她被被子壓着。
許多年後,她還會跟女兒說,你父親是真的很愛你,自己省下來都願意把東西省給你,作為父母,他給你的遠比我給你的要多得多。
生育之後,波樂內心的痛苦沒有更多改變。在這段關係里,除了愛情,她可以付出所有東西,但對方只想要她的愛情 —— 波樂給不了,也沒法給。
在這段錯位的婚姻中,波樂試圖保持一種平衡。
但最終還是失衡了。
出走
生育後,波樂開始不和丈夫同屋,每晚和孩子一起睡。
「我沒有特別排斥跟他的親密關係,但對我來說,這不會讓我感到愉悅,更多是覺得,這是一種我必須完成的任務」。
孩子再大一些,波樂申請了晚班。白天休息的時候,把孩子送去幼兒園後,就約朋友一起出去玩耍,晚上丈夫回家,她已經去上班。兩個人為此吵過許多次,丈夫覺得,波樂「沒有把重心放在家庭」。
波樂覺得,「我已經盡我所能,把能為你做的,和為家庭承擔的責任都做到了,能給的都給了,我想額外保留屬於自己的一些東西。」
1999 年,上網「衝浪」的波樂發現了同性交友的論壇,也結識了越來越多的同伴。
丈夫對此也有所察覺,他開始跟蹤妻子,調查她的通話記錄和聊天記錄。一方試圖離開,另一方抓得越緊,逃跑的那一方越想離開。
很長一段時間,波樂覺得自己困在了婚姻里。「整個人是空的,情感和心是空的,如果說這輩子總會有一個愛的人,那麼那個人在哪裡?不知道。」
她想離開,「如果想迎接一段感情,做一個真正純粹完整的我,那麼就必須剝離一些東西」。
和母親的溝通,讓她堅定了離婚的念頭。
2006 年,母親結腸癌晚期,波樂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照顧母親上。
有天,母親躺在沙發上,波樂倚在她身旁看電視,那是一檔紀錄片,講一個跨性別者接受醫療矯正。波樂忽然問母親,「如果我也是這樣的人,怎麼辦?」
「她說,只要孩子幸福,怎麼樣都行。我整個人一下子就鬆弛下來了。母親那一刻說的話,讓我覺得,他們不會成為我的負擔,反而是我的一種力量。」
波樂走進婚姻前的「一廂情願」,隨之瓦解。
沒過多久,母親和父親先後離世。波樂決定離婚。
她同丈夫攤牌,說明自己的性向,丈夫反應激烈,有一種恥辱感,「他有種『我居然不如一個女人』的挫敗」。同時,丈夫也不理解,認為波樂只是「中間迷了路」,「他說,可以等,等我回頭。」
但波樂一心想儘快結束這個「錯誤」。
婚姻進行到第 11 個年頭,兩人開始長達三年的離婚拉鋸。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男人本就愛喝酒,從此開始酗酒,不喝酒時他挽留妻子,喝酒後開始吵鬧摔打。
最激烈時,男人把匕首架到波樂脖子上,不許她離婚,最終又放下。還有一次,他剪碎了波樂所有的衣服,當着女兒和波樂姐姐的面,替波樂「出櫃」,「她喜歡女人,她是同性戀」,他喊。
兩個人甚至鬧進了派出所,男人一巴掌打得波樂耳膜穿孔。對於這次挨打,波樂有種隱秘的釋然,「我反而放下了,想着,你打吧,就當我欠你的還給你。」
2009 年,男人鬆口同意離婚。但此後每每喝多,還是會打電話或上門羞辱波樂。
離婚後的第三年,前夫因病去世。
波樂一手操持了他的葬禮。臨推去火化前,波樂見了他最後一面,男人看起來有些陌生,像「一個年紀很大的老人」,頭髮花白,整張臉腫脹着。
「我有一瞬間覺得,離開可能對他是一種解脫。我在心裡說,這輩子的好和壞都消了,我們就這樣吧,下輩子,希望他能過得好一點,老天爺對他好一點。」
父親去世後,女兒同波樂哭過一次,為父親抱不平,「你對我爸一點都不好」。
波樂無奈,「很多事情不是我主觀意願能夠掌控的。在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些錯誤,承受能力和各方麵條件沒辦法獨立解決很多問題,等我意識到自己可以獨立解決問題的時候,卻造成了傷害,儘管我努力想把傷害減到最小。」
「我很抱歉,他最想要的東西,我沒辦法給他,強迫不來的。」
被卡在婚姻里的大多數
波樂離開了婚姻,以兩敗俱傷收場。
她覺得,這是自己必經的一個過程。她是一棵樹,一棵自由生長的樹。
傳統的社會性別規範和異性婚姻,都在她身上加碼,「我不需要這些,但就長了出來。你要迎接下一個春天怎麼辦,要把這些東西一層層刮掉和砍掉,如果不把這些東西剝離,我可能過不了這個冬天,因為我生命中的內核已經流失殆盡」。
她的春天萌芽在 1999 年的初次「觸網」。這也是與她年紀相近的拉拉們的共同起點。互聯網的出現,對拉拉們而言,可謂有里程碑般的意義。
她們或是在搜索引擎,或是在交友論壇輸入「同性」「同性愛」類似的詞彙,跌跌撞撞找到了自己的「羊群」,「原來我是這樣的人」,「原來我不是單個的」。
就是在那時,阿楓通過聊天室認識了波樂,當得知兩人同在呼和浩特,她們決定見面。對於初次見面,阿楓還記得自己的忐忑不安,「她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人,但她又掌握了我最隱秘的東西」。
她們相談甚歡,以這樣的方式,一個一個孤獨的點被串連,聚合在一起。
波樂說,最初的聚會有 30 人,滿滿地坐了兩桌。十幾年過去,這些人分成了幾個小團體,但常與波樂一起聚會的也只有這八九個人。她們脾性相投,彼此知曉對方的家庭情況,分享心事,見證彼此每一段人生里程,「比親人還親」。
阿楓是一個 21 歲男孩的母親,直到進入婚姻才意識到,自己對於同性愛戀的真實需求。
她的丈夫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堅持捍衛丈夫或父親的權威。婚後不久,夫妻總吵架,阿楓渴望溝通與和解,但丈夫總覺得「沒什麼需要溝通的」,久而久之,她心也淡了。
如今阿楓有着穩定的女伴,但她仍在婚姻里。17 年前,不用特意找什麼藉口,她很自然地和丈夫分居,也不會掌握對方的財政,「各自為政就好了」。
婚姻里,她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個事事妥帖的妻子,一家三口衣食住行「全包」,定期看望年紀很大的婆婆,維繫和小叔子一家的關係。兒子也更愛她一些,因為相比爸爸,媽媽是可以體諒自己,也可以分享心事的那個人。
但阿楓收回了對丈夫的感情,「我不占你的便宜,我把能做的全做了,我們兩個人走到現在,你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對於離開婚姻,阿楓有着自己的考量。「如果說外面的吸引力對我來說足夠大,而且我有足夠的能力抗擊(出櫃帶來的)風險,那我可能會冒險離開婚姻」。但她自覺「有孩子,現在的家庭結構也非常穩定」,「為什麼要改變呢?」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馮玥是幾人聚會裡常常遲到的那一個,她的女兒還在念書,她要在女兒放學吃完飯才能赴約。
她為自己能夠完美達到「母親」和「妻子」的社會標準滿意。她承包了大部分家庭開銷和家務,每天還有早起做兩頓早餐,給孩子和丈夫的,然後才去上班。
在微信朋友圈裡,馮玥常常分享自己做過的美食,「家長會上,老師還拿我出來表揚,說你們都應該學習這個媽媽,孩子家庭幸福,後勤工作也做的好。我就捂着嘴偷笑」。
在敘述里,馮玥一再將這樣的日常進行「合理化」,但波樂仍忍不住替她覺得累,「太辛苦了,出了這個門,就要不斷掩飾自己的身份,像一個異性戀一樣生活。這種像舞台劇演員一樣切換自己的角色,我是做不到」。
在當下關於同性戀的敘事語境裡,波樂、阿楓和馮玥都容易成為被道德指摘的對象 —— 她們走進了「異性婚姻」,同時發展同性的關係。
「自律」及「健康而值得尊重的社會形象」被認為是公眾接受「同性戀」的必要前提,但單純強調道德完美的同性戀者形象,在某種程度上,容易遮蔽個體所面臨的現實中的具體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金曄路在 2014 年出版的「上海拉拉」一書中細數了中國拉拉身處的困境。
在異性婚姻主流的社會裡,大齡未婚的女性不斷遭致污名。與此同時,在亞洲文化里,女性往往不被承認是性自主權的主體。「對於那些已經與異性結婚的拉拉們而言,一場失敗的婚姻將被看作有負家族期望」。
「不要像我這樣走彎路」
儘管波樂和她的朋友們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選擇,「這條路太難走」是她們的共識。
馮玥至今對家人隱瞞自己「同性戀」的身份,她從不跟女兒聊起相關的話題。同時,馮玥也一直懷抱一種隱秘的期待,「我不希望我的女兒也是拉拉,太辛苦了。」
「如果她是,我也只能接受」,她又補充一句,「但我始終不希望她是。」
波樂承襲了父母對自己的態度,對女兒不干涉太多,她特意找女兒聊起「性取向」這件事。「我的經驗是,你需要在結婚前認真地想明白,你喜歡的是什麼性別,不要像我這樣走彎路。」
女兒顯然早已對自己進行過深入的分析,她告訴母親,「我喜歡異性,很肯定」。
她也接受了母親「喜歡女人」這件事,大學放假回來,會張羅讓波樂好好打扮收拾自己,「不然你怎麼談戀愛啊」。
女兒上大學後,四年過去,波樂一直是一個人生活,還有一隻叫做「豪七」一歲的貓,這個名字來自麻將的術語。
波樂的貓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波樂一直沒有存錢的習慣,工資一多半都花在與朋友的聚會和各類電影音樂碟片上。直到孩子上大學才開始有了儲蓄的習慣,因為想送女兒出國念書。
三年前,波樂的身體開始發出警報。一天夜裡,睡着的波樂突然覺得一瞬間很黑,「好像身體裡的所有的燈一下子全黑了,我感覺有好幾秒鐘,可能心臟停跳了,斷了電的感覺。」
檢查發現,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後來她做了全身體檢,血壓也高。
波樂並不懼怕死亡,「我人生走到這個階段,能做的事,想做的事都做了,很完滿,哪天馬上沒了的話,我不一點都不遺憾」。但她又牽掛女兒,「我們就好像兩隻風箏,線都拉在對方手裡」。
上一段戀愛終結在六年前,她依然渴望一段愛情,渴望一個伴侶,但她同時告訴自己,「沒有必要去為了有一個人陪着去談戀愛,寧缺毋濫」。
周末的 KTV 聚會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周末的飯局結束之後,女人們又張羅着去 KTV 「續攤」,這是飯後常備的助興節目。
在朋友用激揚熱烈的草原歌曲將氣氛炒熱之後,波樂坐在點唱機旁,選了一首齊秦的《懸崖》。
前奏響起,她盤腿靠進沙發,兩隻手握住話筒,半張臉埋進房間的陰影里。
波樂唱,「我不管愛落向何處,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已荒,海已枯,心留一片土」,低沉的聲音漸漸抬高。
嘈雜的房間突然靜下來,女人們停止了交談,兩兩攬着腰,低聲跟着哼。一個女人突然小聲說,「你聽,這唱的就是我們呀。」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全部系化名。)
撰文 蘇惟楚
編輯於陸
拓展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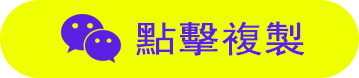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感覺老師還是蠻好的,上次分手都特別難過,後來聽了情感調解之後,我也很快走出來了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