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孩子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着,輕倩地掠過。在那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
------張愛玲
摘自:文/陳功
回憶是一種很透明的東西,透明像是清晨霧霾里的一粒雨,是的,一粒,滴落在額頭之間,睜開眼睛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

我一直在等待我的雨季,許多個小水滴撲朔撲朔地緊湊起來,頃刻間聚成的那場磅礴的大雨。
但雨好像從未來過。
21歲,等待畢業,在廣州並不喜歡的專業里好像時刻經歷着事變一樣的年紀,感染上時代的抑鬱,每天拖着饞喘的身體努力地讓自己行走在教學樓和教學樓之間,對話、微笑、彎腰、寫作、歌唱,幾乎每天都在歌唱,既然這世界上沒幾個人能夠欣賞到我的破鑼嗓,那麼就矯情地自我欣賞。
春天的廣州有一半是青春的味道,流不盡的汗和走不完的路,二十七度的太陽帶來了三十二度的體溫,唯獨少了說話的那麼一個人。大學城梧桐樹長得茂盛的季節,我一個人背着書包坐地鐵去了很多的地方,看白雲山頂的日升,看天河廣場的日落,看北京路迎面走來那些似曾相識幸福的臉,獨自走路一點也不浪漫,抬頭的時候覺得孤獨,低頭又覺得自己憂傷。
我總覺得你在這個世界上擦肩而過的每一個沒有留下姓名的角色,在你閉上眼睛的時候,其實都有機會在夢裡再次遇見。因為懷念,我甚至開始主動地想要做夢,做點什麼夢,什麼樣都好,不需要試圖去掌控另一個世界裡的一切,不需要厚着臉皮懇求運氣給這個「夢」字前加上一個美妙的詞眼,就只是讓我有機會看見那些過去的人。我知道自己再走個幾萬米,也沒有機會再見到那些人。
人生海海,形形色色的臉龐從眼前划過,每一雙眼睛裡都寫滿了錯過。
隨着路邊星星點點的菊花也伴隨着梧桐樹盛開,後來,我又開始了失眠,冰冷而碩大的城市像一隻等待着你落入圈套的棺材,很久沒有再見過流星,空氣里都是回南天遺留下的水汽,站在黑夜裡瞭望不遠處的內環路和貝崗街,平整的瀝青路面寫滿了歡聲笑語,那麼熱鬧,那麼空虛,就連城市深處的站街女都與我無關。
再後來,在城市某個即將瀕臨倒閉,大門前立着雜七雜八的促銷招牌的洗衣店裡,我聽到了鄭鈞的一首歌,《私奔》,「我夢寐以求,是真愛和自由」。回到那個氣氛微妙的男生宿舍,我開始戴着耳機一遍一遍地聽這首歌,在整整聽滿了一百遍的時候,我趕在花落之前認識了她。
晴朗得反常的傍晚,手機上收到了她的消息,白雲機場的位置信息和簡單的一個缺少了標點符號的疑問句,不來接我嗎。
誰都知道她其實拋出的是一個肯定句,有着比藝術和哲學還要肯定的意義。
印象中那幾天我們一直在走路,我很窮,她照顧着我男人的情面,也刻意避開了幾乎一切帶有高消費性質的娛樂方式,儘管對於世界上大多數的姑娘而言,這都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委屈。我們只能走路,從番禺區走到天河區,從珠江的這一頭,走到珠江的那一頭,大城市的美麗風景只有在有人陪伴的時候才能看見,飛機的起飛和降落帶來了一場瓢潑到骨子裡的大雨,印象中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雨,雨水像炮彈,打在我的臉上,打在她的妝上,我在花城匯繁如星辰的燈光下面,將一隻耳機塞到她的耳朵裡面,連同鄭鈞的那一首歌。
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後的信仰,潔白如一道喜樂的光芒,將我心照亮。
我自戀地認為這首歌就是寫我和她的故事,很久之後我才發現,一首歌的時間太短,根本就寫不完兩個人的故事。
接着是長達半年時間的異地戀,我們每日通話,在相隔了大半個北半球的兩座陌生的城市裡,各自失意,又在另一個獨立的靈魂體上找到了那樣一種,無知,並且廉價的幸福。我幾乎在每一次寶貴的對話後,都加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那句著名的台詞,這個世界是不會為你變的,我就像這個世界,我也是不會為你變的。
多麼愚蠢,一個擁有着健全的思維能力的成年人,竟然會將自己和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五年後我飛越3000公里,從廣州出發,到達了她啟程的那個位置,哈爾濱的太平機場。三萬英尺的風像是穿過巨大的鐵皮刮在了我的身上,我的經濟寬裕了很多,這顆渾圓球體上的科技也進步了很多,我已經扔掉了那隻伴隨我經歷了無數個失眠的夜,我曾經賴以生存離不開一秒鐘的有線耳機,換上了最新最貴的藍牙耳機,金錢買來了更加無損的音質和溫暖的頭等艙座椅,但買不來曾經聽歌時的動情和共鳴,我還是只知道這麼一首歌,單曲循環了一整個旅途。
我在想,如果時光能夠重來一次,當我再一次將一隻發黃的耳機塞進她的耳朵里的時候,她將會是怎樣的一種表情,像另一首歌里寫的那樣,她總是會微笑着看我,或是會帶着些沉默。
時間從未告訴我問題的答案,她離開了哈爾濱。當我走在東北秋天空無一人的街道上,我忽然在一根孤零零的電線杆前站住了為她祈禱,我希望她能夠過得更好,至少不會比從前更差。
在又一場拼盡了力氣的降雨里,我連夜回到了廣州,又在日出前回到了自己背着五十年貸款買下的市中心最豪華的一間單身公寓。忽然有那麼一刻我覺得,世界上沒人愛鄭鈞了,世界上也沒人愛我了,看着整夜整夜伴着我睡覺的電視機屏幕上,那些千篇一律、但我一個名字也說不上來的明星臉,我想,也許不會再有任何人基於緬懷去聽一首兩千年代出頭的老歌,而兩千年代出生的那些新人正好像當時的我那樣,傷心開心,圓滿孤獨,微笑落淚地在應天大街上結伴走着。
時間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大街上以最大的音量所播放的幾乎每一首歌都在無時無刻地提醒着你,你已經被永遠地扔在了鐵軌的外面,而向前行駛的列車,將永遠朝着未知的那個目標開去。
我大學時唯一的朋友來到了這座飄渺的南方城市,我的車子迎來了一周一次的限行,我們坐公交車從大學城到海珠廣場,早高峰擁擠的上班族將我們無情地隔斷,順着向汽車內部不斷划過的每一個肩膀,我最終停留在了最後一排靠窗的那個位置,許久不見這樣的景色,又是一個溫暖的春天,這座雨城好像一連半年都沒有下雨,也許都挑在了我入睡的時間點。我想到了很多事情,多半有關於回憶里的那個人,我想到她背着雙手走在我的身後蹦蹦跳跳着躍過的那層老廣州的石板街,想到我們在上海路忍痛買下的那一疊厚厚的印着小蠻腰的明信片,想到分別的那天我送她進到機場安檢,回來的路上在地鐵上看見的那個站起來打着太極拳的老人,臨別的時候我送她一個吻,我告訴她,等下一次花開的時候,我和你就從家裡把戶口本偷出來,去民政部登記結婚。
我想到機場大巴從落地窗下划過時,她回頭對我所發出的那樣一句沒有收到答案的疑問,她說,廣州花開得很早,從冬天到夏天,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你這個人想起一出是一出,也不知道到時候能不能準備好。
我和朋友喝了很多的酒,從酒吧,到燒烤店,再到酒吧,在如永恆的命運哲學一般的循環往復里,無數瓶啤酒下肚,我們的話題終於從成年人的房子、車子、工作和戶籍,迴光返照般回到了我們背後的一抹倩影永遠地遺留在的那個年紀,春痕逐漸褪散的年紀,我們開始談夢,談理想,談對這個世界的那些未完成的期待,談回憶里僅存着唯一的那個姑娘。
朋友賣力地將煙吐成一個一絲不苟的圓圈一樣的形狀,用雪碧壓住白酒的余勁,他說,你知道吧,當時你說中了,要找我借錢墮胎的時候,我心裏面還有些納悶,我想這事是不是這女的在給你下套,哪有那麼容易中的啊,我跟一女的三年了,從來就不戴套,一次都沒中過。說完他開始哈哈大笑,我愣在酒桌上半秒,也開始隨着他笑,笑着笑着就開始哭。朋友說,你怎麼了,不會真被我戳到痛處了吧。我說,你他媽二手煙太烈了,熏得老子眼睛痛。
一肚子的酒,酒精原來根本就醉不了一個打自心裡逃避去醉的人。那一刻我才徹底清醒,回不去了,所有的過往在我的身後開啟了像鑽石光芒般耀眼的一道門,但門裡面早已經空無一人,而所有的光,只是為了向前路上的指引,而不是向後路上的留念。
你知道天底下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嗎,欺騙、麻木、焦慮、抑鬱、失敗、錯信、虛無、絕望,都是的,又都不是,最痛苦的是錯把一段美好的故事寄托在參與到當中的每一個獨立的個體身上而不自知,美其名曰念舊情。
每一個活在回憶里的朋友們,你一定要記住這麼一個基本的邏輯,人們總是在懷念十八歲、懷念二十歲、懷念十二歲,歸根到底,你只是在懷念那樣一個錯過就不再回來的年齡。跟人沒有關係,跟人沒有關係,跟人沒有關係,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根本就不夠。總看見一些文章聲嘶力竭地控訴什麼被從小的朋友欺騙利用,幾十年的感情難道還抵不過啥啥啥之類的,我想說你活該,誰規定了成長的設定就這麼簡單,小時候遇見的都是好人,長大了遇見的都是壞人?那人活一輩子也太沒勁了,前半生交心,後半生虛情,哪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晚最後,我發瘋一樣地幹掉了一整瓶紅星二鍋頭,朋友覺得我瘋了,但我心裡明白,這瓶酒是為他幹的,準確地說,是為我們過往那些如浮雲一般美好而短暫的情誼而乾的。我拍着他的肩膀,告訴他自己沒辦法再多陪他一會,明天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沒有挽留我,傻子都不會在這樣直白的一句潛台詞下挽留一個人,酒勁漸漸上來了,平坦的六車道變成了十二道,我騎着一輛自行車沿着小蠻腰為我指引的方向前進,公園裡有長期露宿街頭的流浪漢和一個抱着吉他的賣藝歌手,迎着晚風唱beyond的《光輝歲月》。
廣州六年,除了那幾句對於對方長輩常用的問候語外,我還是不會講任何的粵語,但簡單的粵語歌詞還是聽得懂的:
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
願這土地里
不分你我高低
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
是因它沒有
分開每種色彩
酒醒後我廉價處理掉了自己的寶馬五系,買這輛車的原因是當時我們走在大學城的時候,路面駛過來一輛喇叭響個不停的三系,經過人行道絲毫不減速,擦過了她潔白的像蝴蝶一樣的長裙,我沿着馬路寶馬車離開的路徑飛奔大罵,撿起石塊砸在排氣管轟隆隆留下的尾氣里,最後我義正嚴辭地答應她,終有一天,我會開上比三系更高級的寶馬車,讓你再也不會被別人擦花裙子。
我以落地八百的價格在二手市場買了一台自行車,但平時很少騎,漸漸習慣了走路上下班,每天凌晨太陽還要升起之前就要起床,穿過大半個獵德,到達那座高達五十八層的寫字樓,我的職位升得很快,職員、主管、董秘、經理,樓層也升得很快,在五十六樓的高度,空氣清朗的日子低下頭能看見小半個廣州城。
在某種程度上,我理應感到幸運,沒有幾個一窮二白的小男孩能夠僅憑一己的努力在這座冰冷的一線城市站穩腳跟,而我已經站在了雲層。
我遇見了另一個女孩,和她長得很像,不只是長相,各方面都像,身高、性格、愛笑、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發音,梨花頭。
女孩的歷史並不清白,公司里散播着她靠陪睡一路上位的傳言,但是我不在乎,我或許明白她期待着從我的身上得到什麼,我也明白自己期待從她身上得到些什麼——那就是她的影子,從另一個平行時空而來,在我的空氣里不斷地錯亂交結,擰成了一團難解的麻花的影子。
為了使影子現形在更加顯眼的地方,我開始帶着女孩重複那些我曾經與她做過的一系列事情。於是詭異的現象發生了,一個年少多金的男人,以及全身奢侈品的女人,在七十塊錢一晚上的大學城學生公寓裡約會,在城市郊區一塊貧瘠的土地搭着廉價的帳篷約會,在花城匯下十二塊錢一碗牛肉麵的路邊攤上約會。
所有人都覺得彆扭,不只是這個女孩,就連我自己,也覺得彆扭。
我們去過了幾乎我和她去過的所有地方,以記憶里存在過的每一種方式,在相處的最後一段為數不多的時日裡,我其實已經能夠預感到一些事情即將發生。但是我不在乎,這樣的一個姑娘,她的未來在哪,另一個男人的床上或者車上,吃着人均兩千的自助餐還是人均一百的路邊攤,戴着她最愛的卡地亞的鑽戒或是lv的最新款皮包,這些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是能不能在迎來尾聲的使用期限內將我應該完成的一切全部完成。為了使留給我的時間儘可能延長一些,我開始向她不停地掏出那些寫滿了數字的支票,五千,一萬,十萬,二十萬,我不在乎,我每天拼盡全力地將回憶抹得一乾二淨,在一張細碎的白紙上列下還未完成的那部分任務清單,我想,只需要再去一趟哈爾濱,在飛機上將鄭鈞的《私奔》塞在女孩的耳朵里,在飛機安穩地降落在太平機場之前,所有的這一切就可以被永久清零。
將所有都清零,關於這裡的一切,接着我離開廣州。
我最終的願望沒有達成,留下了一個莫大的遺憾,女孩怡然自得地挽着董事長的肩膀出現在寫字樓的每一個樓層,像只春風得意的天鵝一樣在三千個職工眼前分別宣示了一遍自己的主權。經過五十六樓的時候,她停留的時間格外地久,我們也對視了很久,我不知道她在那樣的一刻心裡究竟想着些什麼,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什麼。
我打印了一封長長的辭職信,在女孩的眼前交到了五十八樓的董事長手上。
廣州還是那樣的一個廣州,離開以前,我騎着自己沒用過幾次的自行車幾乎繞城市飛馳了一整圈,眼睛裡面出現了一些畫面,足夠地立體,但最終穩定地和現實畫面重疊在了一起。
天河廣場沒有變。
珠江沒有變。
小蠻腰沒有變。
北京路也沒有變。
我漸漸找不到自己的影子了。
我買了回到四川的單程飛機票,2019年,我離開了廣州,從此再也沒有人和我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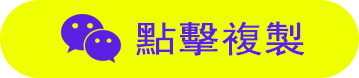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情感機構有專業的老師指導,我就在老師的指導下走出了感情的誤區,真的很不錯!
如果發信息,對方就是不回復,還不刪微信怎麼挽回?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