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晚上回到家,看着空蕩蕩的床,腦子裡「殺了那個男人」的念頭愈發強烈。
這個念頭燃起,隨即熄滅,再次燃起,如此反覆。

張海把生平經歷里,他所認為「說話算數」的機構過了一遍:警察不管,佛祖不管,還找誰?
想了一夜,最後他把視線停留在家裡的電視機上。
第二天,張海給孩子做好了飯,翻了翻衣櫃,找到自己唯一一件西裝,那是當年他結婚穿的。
張海把這件西裝拿在手裡,想了想,又放了回去。他跑到大哥家,借了一件。然後買了去市裡的汽車票。
一周後,張海上了當地調解家庭糾紛的電視節目。
屏幕中央,張海對着主持人,把妻子不回家的事講了一遍。兩個專家坐在觀眾席最前,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如果感情實在不和,應該離婚,學會放手。」
錄節目時,張海很緊張,不停點頭。
從錄影棚出來,張海啐了一口,「說的全是屁」。
上電視,在村里是了不得的事,鄰里沸沸揚揚,人人都知道「張家老二的女人跟野男人跑了」。
但節目播完,張海的妻子還是沒回家。
那天以後,開始陸續有村民告訴張海,「我看到你老婆和那男人上街了,都不背着人了。」
張海把兩個孩子先接回了自己父母家,自己正常去廠里上班。
另一邊,他發現自己殺人的念頭已經完全壓抑不住。他不知怎的理出一個邏輯:那個男人不死,老婆就不會回家。
1
我當了6年獄警,張海是我打過交道的1000多個犯人里,最規矩的一個。
如果不是看過他的檔案,我很難想象,他會是個重刑犯。
第一次見到他,是2016年的5月。那天上午,他剛從看守所里和十幾個新犯一起被送進監獄。
我路過一樓大廳時,他正蹲在牆角,被一個老犯摁着頭把頭髮剃光,只剩下一層青楞楞的頭皮。
我放眼掃過這一片新犯,目光和張海相交。
他抬起頭,沖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浮起一層靦腆和討好。
新犯入獄,獄警必須和他們進行「十必談」。這種談話是談心摸底,也是教訓和下馬威,警告他們來到監獄後要守規矩,好好改造,別惹事端。
談話工作由易到難,我看張海面相憨厚,就讓他第一個來辦公室談話。
辦公室里,新犯的檔案早已在我桌上擺好。
我從中挑出張海的,剛翻開第一頁,心裡「咯噔」一聲,先沉了一半——
「張海,男,L市X村人,故意殺人罪,無期。」
受害人當場被三刀捅死,兩刀在肚子,一刀在脖子,當場在床上咽氣。
殺完人後,張海轉身去了最近的派出所投案自首。
根據值班民警的記錄,張海衝進派出所那晚,「滿身是血,提着一把魚片刀」。
我正看着卷宗,張海已經走進辦公室。我抬頭,仔細打量了他一番。
他不到1米7,身材敦實,眼睛細長,右頰上還有一片麻子。雙手幾乎完全廢了,各自只有一個拇指是完好的,其餘地方是兩團糾纏成畸形的肉塊。
我故意把臉沉下來,問他知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叫來。
張海點頭如搗蒜,說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他自首時沒想到能判無期,這條命是政府給的,絕不會在監獄裡惹是生非。
我「唔」了一聲,又翻了一頁他的檔案,若無其事地問:「說說吧,你這殺人是怎麼回事?」
他的笑意立刻消失,換上一副愁容,「警官,男人遇到這種事,誰不得殺人?」
我拍了一下桌子,問他殺人還有理?
張海沒回答,突然抬頭問,「警官,我這個無期,以後還能不能出去?」
我猶豫了一下,如實告訴他,如果表現足夠好,減刑之後,最快坐個十幾年就能出去。
張海的小眼睛裡泛起了光,聲音也高了八度:「警官您放心。我現在活一天就是賺一天,一定好好表現,早點出去。」
還沒等我說話,他就自己念叨起來,「大兒子四年級,小女兒二年級。要是坐十幾年就能出去,說不準還能參加兩個娃的婚禮。」
說這話時,他用兩隻手的拇指盤算着。
我盯着他看,忽然發現張海的長相其實很有意思。
他的眉頭是天生向下,略帶八字,好似永遠皺着一樣,哪怕是在笑的時候,都是皺着眉頭。
2
在上了調解家庭糾紛的電視節目後不久,讀高中的侄子對張海說,二叔,你應該去看心理醫生。
這是他婚後第8年,失眠第3個月。
他趴在床上,干瞪着眼,一直被一個心病所困擾——如何讓妻子回家。
3個月前,妻子出軌被他發現,說心已經不在這個家了,要求直接離婚。
張海強硬地拒絕,表示寧可死掉都不能離。
老婆沒說什麼,當晚打包行李,住進了那個男人家裡。臨走時撇下一句話:「你如果想好離婚了,可以隨時來找我。」
張海崩潰了,但並不死心,他決定嘗試所有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像自己人生前幾十年做到的那樣。
張海乾什麼事都比別人更難。他出生在一個偏遠村莊,家以務農為生,一共三個兒子,他排老二。
童年時期,冬天家裡燒火炕,張海從床上摔下來,雙手插進炕里。從衛生所出來時,醫生說張海這輩子只能用剩下的兩個大拇指過活。
80年代,張海沒讀完小學便去了縣城打工。因為雙手殘疾,沒有地方收他。
張海不要工錢,只要管吃住就行,終於找到了第一份工。後來他又跑到省城,學了些手藝,陸續也賺到一點錢。
有個老鄉看他能吃苦,讓張海跟着他去當地一家大型國有煤廠試試。
起初張海是夜班看大門的,工資很低。時間久了,他跟開弔車的大師傅混熟,沒事就湊在邊上專注地觀察。
大師傅坐在駕駛艙里笑他,「殘廢還想學開車?」
張海對着吊車一盯就是大半年。終於有一天覺得十拿九穩了,跑去跟大師傅說:「開車不難,我也行。」
大師傅笑了一通,說要跟張海賭半條煙。
張海認了賭,一上車,手忙腳亂,差點把吊車撞到牆上。煙賭輸了,可大師傅看張海是真想學,開始慢慢教他。
沒過多久,廠里有人退休,空出來一輛吊車,張海毛遂自薦。當着眾人的面開了一遍,又說,只要能開弔車,自己只要七成工資。
領導們盯着他的手,又看看那輛車,猶豫了半天,還是同意了。
張海拿了兩年多的七成工資,後來工廠改革,統一化編制,張海被稀里糊塗地算進去,成了正式員工。
他坐進吊車裡,一開就是十幾年。成了資深老工人,最後每月能到手六七千塊。在那個地級市是絕對的高收入。
開上工廠吊車的第五年,張海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那陣子,張海的老婆因為家裡出事,投奔到他們村里一個遠房親戚。沒兩年,那個親戚搬了家,因為無依無靠,就有人把她介紹給了張海。
張海常常跟人提起,他老婆長得很漂亮,像掛曆上的影星,如果不是因為沒有着落,根本輪不到自己。
兩人在一起沒多久,就張羅着結婚。按照當地風俗,張海家要出彩禮錢,十幾至二十萬起步,張海根本出不起。不過因為是外地人,他老婆不知道規矩,沒要一分錢彩禮,稀里糊塗地嫁了過來。
那陣子,村里人都在背後笑話張海的妻子,說她太傻,嫁了個又窮又殘廢的男人,還沒要彩禮錢。
這一句話,讓張海記了很多年。
那次婚禮,光是酒席和喜糖就花了5萬8,讓張海家欠了別人1萬8。用張海的話說,把他爸的棺材本都貼進去了。
張海那時沒正式被工廠錄用,工資低。結婚請了兩天假,結完婚第三天,他跟表哥借了500塊錢,又回去上班。
他開始拼命掙錢,也努力省錢。先是把婚禮借的錢都還了,然後不停給老婆買禮物。村子裡誰家媳婦戴了金項鍊,銀手鐲,玉墜子,他都記在心裡,省吃儉用也得給老婆買。
後來家裡鬧分家,嫂子看不上張海,嫌他是個殘廢礙眼。張海老婆也勸他出去單過,說搬出去了,就有了自己的家,窮一點沒事,慢慢熬,總會有好日子。
這句話說服了張海,「我想也對,起碼是該有個自己的家了。」
那是最苦的一段日子,張海很少能夠回家吃飯,他在宿舍小屋裡買了煤氣罐和鍋,買點豆腐,或者菜葉,回來一炒就是一個菜,就着饅頭,便是一餐。
最節省的一個月,張海只給自己花了150元。到了月底實在沒錢,他便拿饅頭沾着鹽吃。
在掙錢和家人之間,張海選擇先掙到錢。除了比較長的節假日,張海基本很少回家。平日家裡只有兩個未經世事的孩子,以及他的新婚妻子。
沒過幾年,張海成了村里最先蓋起三層小樓的人家。即使如此,他依然難得能回去一趟。
每當和人聊起這段往事,張海都會撓撓頭,很費解地說:「我也不知道這是咋回事,窮日子熬過來了,倆孩子也有了,我工作也穩定了,什麼都好了,她怎麼就不回家了呢?」
想來想去,張海覺得,一定是因為那個男人迷惑了妻子。
3
妻子本人拒絕和張海進行任何溝通。張海想了幾天,決定報警。
站在鄉派出所門前,張海看着藍底白字的牌匾,猶豫了10來分鐘,還是進去了。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進的派出所。
接待他的,是個40多歲老警察。
兩人面對面,張海支吾半晌,擠出一句話:「政府,我老婆跟別的男人跑了,我要讓她回家,你們管不管?」
老警察沒開口,先笑了一陣,說管不了,低頭看起手裡的本子。
張海沉默了半天,最後說,警察同志,我是來報警的啊。
警察又笑了,說你要是想離婚,可以去法院告她。如果想複合,就找她好好談談。你報警了,我也記錄下來了,可這不在我們的管轄範圍啊。我們基層警力很寶貴,你不要因為這種事浪費我們的時間。
張海不懂什麼是基層警力,也不懂出軌到底歸不歸法律和警察管,但他已經沒有膽子和臉皮再糾纏下去。
他原本以為,警察會像電視劇里一樣,幫他呵斥妻子,他也就能有一點底氣。
但現在,張海覺得民警看着自己笑的時候,就好像在看着他頭頂上一頂無形的帽子。
他受不了這種意味深長的眼神,也不敢再多說話,起身離開辦公室。這次報警全程用了不到5分鐘。
走出派出所的院子,正好是鎮上一條繁華的街道。張海快步走向長途汽車站,路上他一直沒抬過頭。
那天,他的腦子裡第一次蹦出「殺人」兩個字。
張海反應過來,嚇了一大跳,腦門起了一層冷汗。
鄉鎮派出所給不了張海「解藥」。隨之而來的,是心病發作後的「陣痛」——妻子連續好幾天沒回家了。
張海的兒女發現了這一點,哭着問媽媽去哪兒了。
他腦子一熱,想衝進那戶男人家,把妻子直接拽回來。剛出家門,走了幾步,張海就後悔了。
「她只是被那個男人迷惑了,只要有辦法,怎麼都會回來,沒必要搞得雞飛蛋打。」
很快,張海就想到了一個辦法。農村的電視劇里,常有遇到大事要去廟裡拜一拜的場景。他覺得電視台里放的東西肯定沒錯。
張海去了當地一家香火很旺的寺廟。進了廟裡,幾名僧人圍上來。張海說,自己遇到了很煩心的事,想求佛祖擺平。
僧人先讓他燒香拜佛,消除業障。然後從玻璃櫃檯里拿出三種香,指了指,說有399的三炷香,699的六炷香,1299的九炷香。
張海一點沒猶豫,直接買了699的六炷香。他覺得這幾個數字最吉利。
全都燒完,僧人們遞過來幾本經書,讓他回去看。
張海說自己不太識字,僧人們就給他講了幾個佛經里的故事。
僧人把故事講到一半,張海就強行打斷,問了兩個問題。
「我老婆出軌了,佛祖能把她拉回來嗎?」
「我好想殺人,到底該咋辦?」
聽到第2個問題,幾個僧人搖搖頭,讓張海原路回派出所,去自首。
「我他媽的還沒殺人呢,我自首什麼啊我?」罵完,張海頭也沒回地走出寺廟。
在監獄裡,給我講起寺廟那天時,張海說,他在掙扎這麼久的過程里,警察也好,老婆也好,他都不怨。他知道,老婆要離婚,誰都沒法管到。
但他唯獨記掛着那一天,被和尚騙去了699塊錢。和我念叨過好幾次,說廟裡和尚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4
同樣也是因為錢,張海入獄後的第一個月,就給我惹上了麻煩。
家裡給張海存了1800塊錢,讓他在監獄裡用。
張海找過我不下10次,想把這1800返給家裡,老人孩子都要用錢,他會好好攢分,用不着。
我幫他辦了兩次,因為相關規定不允許,都沒辦成。
張海心裡不甘,有一次趁着副監獄長來視察,直接跑到副監獄長面前說了這事兒。
副監獄長不分管這一塊,不太懂這是違規的,想當然地覺得可以,然後把我批評了一頓,說要滿足犯人合理需求,儘快辦了。
結果另一個分管的副監獄長不簽字,說不可能辦理。
我當時不太高興,跟張海說,我前前後後跑動,結果你還去找副監獄長把我批評了一頓。我好心餵了驢肝肺,這不是害我嗎?
張海很愧疚,特地找了兩個民警,讓他們幫忙跟我解釋道歉。
半年之後,我幫他辦理了家裡的低保和監獄補助。
因為這事兒,張海每次看到我的時候,老遠就大聲打招呼,主動要幫我打掃辦公室,燒水拖地,都被我婉拒了。所以他就更覺得虧欠我的,對我格外熱情,怎麼說都沒用。
這件事,讓我察覺到張海的骨子裡執拗的一面。
拼命滿足自己的訴求,卻又欠缺考慮,因此做錯事了,又拼命想要補救。
正是因為這份執拗,才會釀成他身上背負的這起血案。
對於絕大多數男人來說,遇到妻子出軌,第一反應是離婚,最壞不過是打官司,分家產,爭孩子的撫養權。
但這些道理在張海身上完全不適用。對他來說,這個婚姻,是他的「家」——他經常跟我提起這個字。
所以當老婆出軌,即使到了最後,他也只是刺死了那個男人,把那人定義為「拆我家的人」。
而出軌的老婆,對他而言仍舊是家裡人,「傻傻的,她被那個男人騙了而已。」
5
張海的這種偏執,連精神科醫生都沒法治。
報警無效,拜佛受挫,這期間過去了快一個月,妻子依然住在那個男人家。
張海掛了城裡大醫院精神科的號,前後一共看了4次。
對着心理醫生,張海把自己的生平,娶媳婦後的日子,老婆出軌的過程,報警拜佛找媒體的挫敗,全部原原本本講了4遍。
醫生給他進行了心理疏導,開了緩解焦慮的藥。
張海從城裡揣着藥回到家時,天色已晚。他關了燈,一個人躺在床上,怎麼都睡不着。這樣的不眠之夜持續了快一周。
心理醫生說了很多話,張海只記住四個字:情緒排解。
張海覺得任何情緒排解都是假的。「我必須去殺人,如果不殺人,老婆回不回來另說,我自己都快自殺了。」
這個念頭旋即消失。「憑什麼要我死?我還要養孩子,養老婆。要死是那個男人死。」
次日天黑,他提着一把鋒利的魚片刀,一腳踹開妻子情夫家的大門。
他的妻子正和那個男人一起睡在床上。
張海沒一句話沒說,舉起了刀,一刀捅進了妻子情夫的肚子,然後拔出來,又捅了一刀進去。男人肚子上已經血肉模糊,張海沒有再往那裡捅第三刀,他把第三刀扎進了脖子裡。
殺人後,張海再次來到派出所,這次是去自首的。他以「故意殺人罪」被批捕。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6
張海的獄中生活,果然如他所言,「好好表現」。
他幹活積極主動,從不與任何人好勇鬥狠,入獄後第3個月,就被調到了監區的勞動組。
勞動組負責所有犯人的清潔雜活,每個月的計分考核都很高,也能拿到不錯的勞動報酬獎勵。
每次在監區看到張海,他都在默默地拖地擦窗,積攢着可以給他換來減刑的每一分。入獄後第6個月,張海拿到了監區第二檔的減刑分。除去幾個內務組長、電工,張海的分數是全監區第一。
有一次偶然聊起,問他監獄裡的伙食吃不吃得慣。
他連連點頭,說監獄裡頓頓吃得飽吃得香,比在牢外還舒服。
監獄的伙食要說「吃得香」,那是真算不上。
每頓飯是一個監房12個人一組,提着兩個桶去打,一個桶裝米飯,一個桶裝菜,菜是湯湯水水一鍋端,方便泡着飯吃。早飯也就是鹹菜饅頭,稀飯雞蛋之類,都是監獄內部專門由會做飯的犯人組成的一個伙房監區自己燒的,味道可想而知。
張海卻顯得誠摯,說自己年輕時在工廠打工,一頓飯六個大饅頭,沾點鹽就能一口氣吃完。哪像監獄裡,頓頓有好菜吃。
我覺得,他大概是把殺人入獄當成了解藥。
半年來,張海在監獄裡的一言一行,都讓我很難把他跟一個連着三刀把人捅死在床上的「狠角色」聯繫在一起。
入獄一年後,張海已經完全適應了監獄裡的生活,並且和家裡保持了基本的通信。
兒子和女兒由老兩口來養。老人本就沒什麼收入,之前因為分家有糾紛,連低保都沒法領。後來還是監獄出面,跟地方政府協調,給他的子女提供了一份上學補助,以便讓張海能夠安心服刑。
當然,監獄也有自己的需求,特地將他的事情作為正面典型,對全體犯人進行宣傳,其中還需要拍一些宣傳用的鏡頭,要他說一些感謝監獄關懷的話。
那陣子我去張海老家送過一次補助,還錄了幾段家裡老人和孩子的小視頻,回來給他看。
視頻里沒有張海的妻子。出事之後,她直接離開了家。
對於現代監獄來說,防止犯人越獄,不只是高牆電網,連坐監控;而是從心理上掌握犯人的動態,有無言行異常,有無情緒波動,有無家庭變故,有無越獄逃跑,或者消極求死的念頭。
對於張海這樣的無期徒刑犯人來說,情緒波動是經常性的,需要隨時做好觀察和交流,防止他因為過長的刑期而想不開。
老婆沒在家,這種會強烈刺激到他的事,自然是能不提就不提,以防生出事端來。
沒想到張海有一次主動跟我說,她走就走吧,因為老婆的事情他才會進監獄,他爸媽怎麼可能她好臉色看?
話音剛落,他又補了一句:「等我出去了,再找到她過日子。」
7
一直到了最後,張海都沒跟我說,他是怎麼發現老婆出軌的。
我問過兩次,他搖搖頭,說算了,人死燈滅,他不想提。
再後來,張海再沒跟我提過他老婆。偶爾被我看到,他都是在收工休息的時,看着窗邊,一個人發着呆在笑。
他更喜歡跟我聊他的一對子女。
我見過那兩個孩子。給張海家裡送補助那天,我開了兩個多小時車,才到張海的父母家,在一個邊遠的小山村。
老兩口住在一間老房子裡,屋子很破舊,幾乎看不到什麼家用電器。那棟張海蓋起的三層小樓早已不知去向,他的兩個孩子就住在這裡。
進屋時,兩個孩子跑出來直直盯着我,穿得有些髒兮兮。
我說起張海在監獄裡的情況,張海父母只是「嗯嗯」的答應,沒說任何其他話。
整個家裡,封閉而貧困,張海曾經存在過的氣息,早已消散不見。
那天回到監獄,我對張海說,你放心,他們過得都很好。
我讓張海來辦公室,用電腦放了一段在他家拍的視頻。
屏幕里,兩個孩子奶聲奶氣地說:「爸爸,我們等你回來。」
放到這兒,張海的眼淚「唰」地一下落了下來。
我給他倒了杯水,沒說話。
他把視頻看了三遍,整張臉都哭得通紅,抽着鼻子對我說:「隊長,其實我啥都看開了,可就是心疼家裡倆孩子,是我這個當爹的對不起他倆。」
「你說就為了這事,把自己半輩子搭上了,值嗎?」我嘆了口氣,還是問出了這句憋了很久的話。
「不是值不值。」他一邊抹着眼淚,一邊搖了搖頭,「我殺他,是救我自己。起碼現在我活下來了,我的孩子還有個盼頭。」
我篤定地相信,監獄裡這份無期徒刑,已經是張海找到的解藥。
直到那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8
那是去年5月的早上,我照常進行審閱犯人信件的工作。
一封信擺在我面前,牛皮信封,右上角貼着一張老式郵票,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
信封看似很厚,我拆開一看,只是一小疊信紙被折了三折,硬塞了進去。
所有從監獄內外流通的信件,每一個字都必須經過我們獄警的眼睛。確認沒有任何問題之後,才被允許收寄。
收信人是張海。
前三頁是張海的父親寫的, 張海的小兒子寫在第四頁,再後面,則是幾張空白的信紙,連最上頭的紅膠都沒撕開。
信的內容沒什麼違規之處,我掃了幾眼,就扔到了一旁,準備等會交到張海手裡。
就在這時,鬼使神差地,我突然覺得哪裡不太對勁。
我重新打開這疊信,反覆讀了兩遍,很快,有個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張海的兒子後面那頁白紙。小孩子剛學會寫字,下筆很重,在後面一張紙上留下筆痕。
那張白紙上,倒數第2行,留下了較為明顯的「此致敬禮」的筆痕。
古怪的是,在兒子那頁信上,「此致敬禮」卻出現在倒數第6行,比留下的筆痕位置高了不少。
而兩張紙之間,最上面布滿細密的,紙張撕去後留下的碎紙毛邊。
原本在兒子的信後,還應該有一張紙,卻被人為故意撕掉了?
我隨手拿起了一根鉛筆,開始在後面的一張紙上描了起來。
一封隱藏在白紙中的密信被慢慢描出。
我瞪大了雙眼,從位置上一躍而起。
讀完描出來的內容,我緩緩又坐了下來,沉默了很久,拿起桌上的內線電話,撥到了另一側的監房中。
進到我辦公室的時候,張海顯得有些侷促。
「隊長,啥事啊?」
我將信遞給了他——當然,是沒有後頭白紙的。然後隨手點了一根煙,坐在椅子上,靜靜地看着他:「家裡來信了,你就在這看吧,看完有沒有要回信的,跟我說聲。」
他很高興,雙手接過信,沖我連連道謝,然後抽出信紙,就站在那兒眯着眼睛,一字一句地看了起來。
信不長,他很快就看完了,將信疊起來塞回信封,「沒事,不用回,家裡老人小孩一切都好,低保和補助都按時拿到,都好着呢。」
說着,他撓了撓頭,又露出了招牌式的笑容。
我點點頭:「那就好,回去吧。」
「謝謝隊長。您費心了。」
他沖我鞠了一躬,轉過身,準備離開辦公室。那一刻,在我身前的抽屜里,正攤着一張白紙,紙上被鉛筆塗滿,顯露出深深淺淺的稚嫩筆跡。
我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把這張紙截了下來,沒有交給張海。
按照監獄規定,如果犯人和親屬之間的信件有任何違規的地方,獄警有權予以截留和銷毀。
而這張被撕去的紙上,孩子寫了一些別的事情:
叔叔想來霸占家裡的房子,奶奶的身體又病重了,妹妹在學校被很多同學欺負,天天回來哭。
最後一句是「寒假的時候,媽媽把我和妹妹都接過去了,給我們買了很多好吃的。」
「對了爸爸,媽媽有了新的男朋友,對我和妹妹都很好。」
▲
張海雙手殘疾,但他堅持要學開弔車,拿正式工資。這人身上,有股狠勁。
前半輩子,執念成就了張海,讓他覺得只要發狠,沒什麼辦不到。
後半輩子,還是執念,這次卻困住了他。為了挽回妻子,他四處求藥:找派出所、拜佛、上電視、看心理醫生…直到殺人入獄。
成就過他的,最後也將他毀滅。
台灣導演楊德昌拍攝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男孩認為遭到了女孩的「背叛」,他想到的解決方法和張海一樣——殺人。結尾時有一句台詞,我記得很清楚——「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
張海以為殺人是他的藥,高牆能治癒自己,其實現狀並未改變。一封信打破了一切。
這是張海的求藥之旅,但出發前,他就做了錯的診斷。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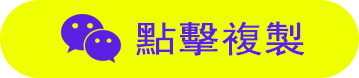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確實不錯,挽回了不少瀕臨離婚的家庭!
可以幫助複合嗎?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
如果發信息,對方就是不回復,還不刪微信怎麼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