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 陝西韓城旅遊微信 你才不是古城的過客
吾城 | 有故事的韓城 有味道的旅程
《党家圪嶗》
黨康琪

第十二章 紀秀來了
生意果真又一天一天好起來了,寬老闆也喜歡天天來坐。寬老闆愛擺龍門陣,但身為大老闆,老給掌柜賬房夥計扯閒篇,不僅少了威嚴,有時還誤事。有人勸寬老闆,說這樣不好,寬老闆聽進去了。但出去擺,別看這碼頭上,還難找對象,又不是人家說書的;老憋着,也實在難受。來了黨林,天天站櫃檯,不出門,就有個忠實聽眾,當然,黨林也不寂寞了。閒時,寬老闆便天南海北地說了開去。忙時,還樂意幫幫手。
北方話好懂好學,寬老闆在中原跑了幾年,早都會說了。陝西話當然是北方話,但陝西夏陽有些話卻不那麼好懂。黨林翻秦嶺以前,不敢見人,幾乎不用說話,一翻過秦嶺,便時時感到自己的話難懂了。比如,見人難免打招呼,開口就是:「你自摸七?」回答別人,常常要說:「不謝。」別人覺得話搭不上茬,總是瞪眼看你,那意思再明白不過:「您老倒是說什麼呀?」於是,黨林便開始細聽別人的話,學着別人的說法,努力避開別人聽不懂的自己嘴裡冒出的詞兒。你想,不這樣還怎麼做了幾個月的生意?
一天,寬老闆正要說自己當年在家鄉和亂兵打交道又挨打罵又受尊敬的事時,突然起身要走。黨林正聽到興頭上,急得就喊:「你自摸七?」喊得寬老闆回頭瞪起了眼,道:「你說什麼?」黨林先愣了一下,很快又笑了起來,道:「我說我正聽得上勁,你幹什麼去。」寬老闆道:「噢,這麼回事。我,我上茅房,要告假?」黨林道:「謝啦。當然不用。」寬老闆道:「這有什麼謝頭。」黨林又笑了起來:「『謝啦』就是知道啦。快去吧,別耽誤了你的正事!」
這兩句話勾起了寬老闆對夏陽話的興趣。方便回來,賣開關子,說:「整天聽我的,我看我得打住,先給我說說你們那兒的話。你不說,我也不再說我的事。」黨林哈哈哈哈笑了起來:「那咱倆都憋着,看誰能憋過誰。」寬老闆催道:「別扯沒用的了。快說!」
黨林道:「好,好,我說,我說。我們那兒說知道時說『謝』,不知道自然是『不謝』了。上村學時,先生說讀作『謝』音,寫作『解』字,說古代結繩記事,繩結系在長杆上,事兒不一樣,結兒就不一樣。時間長了,繩結自然多了,能把一個一個繩結說清楚的人反而少了。能說清一個繩結,就是能解開這個繩結。會解的人一邊一點一點解着繩結,一邊同步仔細說明這麼打的原因,也就說清了繩結記載的事件。解繩結不就是了解繩結知道繩結嗎。先生說,這個字義古着呢。記住我剛才急了冒出的這兩句常用話很容易,但我們那兒將『東』讀為燈,將『團』讀為談,將『狼』讀為羅,將『星』讀為歇……每個字後邊還都跟着一大堆同音字,那數目就大了。我天天小心躲避,只怕別人聽不懂,仍出漏子。你看,剛才不還丟了人?這樣吧,我來說一首用家鄉話作的詩,讓你過過癮,自小我爹給我說的,只能聽,我可不會寫……」
黨林正要說詩時,開張那天掃人興的三個混混闖了進來,那個尖嗓子先尖道:「黨老闆,大發了!」黨林迎了過去,道:「一個人開的小店,也就過得去吧。」尖嗓子道:「一個人開的店?我們早就查清了,比雜貨市那邊兩個三個人經營的買夫都多。弄不清這個怎麼混飯?我們頭兒說了,那天你交得太少,還要交那麼多!」黨林正要搭話,寬老闆耐不住性了,先道:「占的是我的地兒,那天你們做的就不在理,還來!你們能不能去做點人活?」
三個人一起上來逼住了寬老闆,尖嗓子道:「罵誰呢?你的錢也翻一番!」
黨林急忙上前護住寬老闆,笑道:「我交錢,你們走人。沒寬老闆的事。」
三人猛撞黨林,讓他讓路,要抓寬老闆。他們覺得寬老闆挺礙眼,仗着錢多人多,愛拆他們的台,這次還公開罵他們,不殺殺威風,不說當下丟人,以後的日子還怎麼過!但是,微笑着的黨林就像根石柱子立在寬老闆前面,一動不動。尖嗓子又衝着黨林喊道:「你走不走?再加一份錢!」
黨林看出尖嗓子是頭兒,一邊笑出聲來一邊抓住他一邊朝外走一邊說道:「見好就收吧,你們不是來要我的錢嘛,我給就是。幹嘛動武呢?」
尖嗓子怎麼用力也掙脫不了黨林的手,另有一個伸手來幫,卻不料被一塊兒拽了出來,往前一送,都差一點兒跌倒。三人一起矮下身來看黨林。
黨林仍笑着,摸出錢來:「都走吧,我給錢,就我的錢,沒寬老闆的事!」那個沒幫上尖嗓子忙的趕緊點頭,接錢,另兩個還在那兒傻着。寬老闆出來喝道:「還不快滾!」三個人這才夾着尾巴溜了。
就因為這茬,隔了幾天,尖嗓子他們叫來背着手的那個頭兒和十幾個持棍的同夥打上門來,砸了黨林的店,最後也砸了尖嗓子的飯碗。
該說那頭兒去南陽城核實黨林身份的事了。也就七八天吧,已經大半後晌,那頭兒領着自己的一干人馬,跟在紀秀後邊下船來見黨林。才幾個月時間,紀秀變大了不少,或許是南陽水土的原因,或許是進了城也開始打扮。她學了她媽的樣,也穿起一身黑衣,梳起髮髻,但衣褲是綢料,沒扎褲腳,腰間又隨意勒綹紅綢,掛了把短劍,英姿颯爽,在一群男人前面很是搶眼。有那頭兒指引,紀秀遠遠就看見黨林的店鋪,上了岸,一邊跑過來,一邊喊道:「黨林哥,黨林哥!」聽得那頭兒一行面面相覷。
黨林迎出鋪子,喊道:「紀秀,你怎麼來了?」
「我怎麼不能來?」
「不是這個意思。」
「還說呢,還不是你的事?」
那頭兒趕了過來,拱手對黨林道:「得罪得罪。」又回頭招手道,「哎——都過來,都給黨掌柜跪下!以後黨掌柜的事就是咱們的事,聽見沒有!」說着,掏出一個十兩銀錠,雙手遞上,「在下張武,有眼不識泰山。還望海涵。」
這場面讓黨林感到突然,頓下不知該如何應對。木廠裡邊,寬老闆一聽到響動,忙趕出來,見了此狀,只站在圈外靜靜觀望。
紀秀道:「給你你就接嘛。他砸了你店,該賠禮賠償呀。」
黨林道:「就覺得禮大了,銀子多了。」
紀秀道:「不大不多!我媽說了,不看在他當年跟我爹練過功夫的份上,就這,過不去。你讓他說句心裡話,打個顛倒,這樣過分嗎?」又回頭對那頭兒說,「我說的對不對?」
那頭兒道:「正是,正是,紀大姑娘說得一點兒不錯。黨掌柜一定收下!」說罷也要跪下。
黨林上前攔住:「你年長,這哪能呢?好,我接。你讓其他各位都起來。」
紀秀道:「這就對了。就是受他一拜也不過分,誰讓他做下沒理的事?」
那頭兒道:「這真是不打不相識,以後有什麼事儘管吩咐。他們幾個還想跟你學功夫呢。」
黨林道:「扈三娘避難伏牛山,周圍一百里的人爭相和她來往;紀秀她爹跟隨她爺爺經營鏢局,捨命保衛南陽城,周圍一千里的人到今天還懷念他們。功夫要學,為人也要學,是不?願意和我交朋友我很高興,但我沒有教過人。真要學功夫,去投扈三娘。」
那頭兒道:「黨掌柜的話我記住了。我服扈三娘,在先不知她在哪兒,我會挑幾個讓三娘指教。還有,領頭惹事的那個尖嗓門我開銷了。紀大姑娘,黨掌柜,那我們走了。」
看着張武一夥離去,寬老闆才走上前來。黨林趕緊給紀秀介紹了寬老闆,又給寬老闆介紹了紀秀。寬老闆道:「久聞扈三娘大名,今日得見紀大姑娘,十分榮幸。」紀秀道:「寬老闆,我哪能受得起你這樣稱呼,你就跟黨林哥一樣叫我紀秀吧。」黨林道:「她年紀還小,沒有在外面闖蕩過。我也覺得叫名字好,寬老闆,你說是不?」
寬老闆道:「好,就叫紀秀。——黨掌柜,我今天對你又有了認識。那個張武的『以後黨掌柜的事就是咱們的事』、『有眼不識泰山』一類話,從他講,大概最貼心了,但這話只講朋友,不講是非。你的答話好啊,扈三娘他們講仁講義,才得到武林擁戴,百姓讚美,哪裡只是武藝高強?」紀秀聽着這話,忽閃着眼睛;黨林不停地點着頭。
寬老闆又道:「紀秀,今天我代黨掌柜為你接風。黨掌柜來這裡快兩個月了,整天只忙了生意,我們也沒有一塊兒吃頓飯。不要推辭,就在廠里,我內人操廚。你們先在這兒看櫃檯,我馬上去安排。」說罷離去。黨林正想着領紀秀到外邊飯攤上去,自己在鋪子裡整天有一頓沒一頓的,實在沒辦法款待遠道而來為自己解困的紀秀。這下好了。
寬老闆一走,紀秀解下佩劍放到貨柜上倒水就喝。黨林歉意地看着,拿過短劍一邊把玩,一邊就給紀秀說開寬老闆的好:說自己如何先在雜貨市安身;如何代賣瓦罐;如何得到宗師傅關照,總攬了賈營這一片鹽務;如何被人擠對;如何僱傭的兩個夥計,一個主動辭退一個不辭而別。說不是寬老闆照顧,還不知道現在成了什麼樣子。聽得紀秀嘖嘖不斷,嘆息不止。
正說着,寬老闆來叫。二人趕緊上了板門,黨林順便去給驢子添草,紀秀跟了過來。那驢子見到紀秀,也搖耳朵甩尾巴的,還昂起頭叫了一聲。黨林說:「和你打招呼呢!」紀秀說:「我知道,一起走了那麼多天,老相識了!」邊說邊在驢子背上摸了幾下。
寬老闆兩位夫人,跟在生意上的是二夫人,小寬老闆十來歲,也就三十多吧。寬夫人很少出來,看見黨林和紀秀進來,她又是讓座,又是倒茶,一邊說道:「我不會做菜,將就了幾樣,不合口就說,可別在肚子裡笑我。」黨林道:「夫人說笑了,怎麼會呢?」紀秀見黨林稱夫人,也道:「夫人客氣了。我空手上門,你這樣熱情,實在過意不去!」寬夫人道:「我們家老闆和黨掌柜是好朋友,黨掌柜的貴客就是我家的貴客。我也聽我們家老闆說過扈三娘,有機會款待她的女兒是我的榮幸。是不?你們說話,我上菜去。」
黨林離家以來的吃食不必說了,只說紀秀,長這麼大,就沒吃過幾次擺得上席面的飯。你想,一個整天舞槍弄棒還要督促兒女也舞槍弄棒的媽,能做出多麼可口的菜?
一邊寬夫人端着,一邊寬老闆介紹說,天熱,準備的涼菜多點,這是糖拌三鮮,這是牛肉片,這是豆豉鮮魚,這是五香肉,這是石花菜,咱們邊說邊吃。再炒三個熱的,隨後就好。說紀秀來得突然,本來應該準備得好點,一下籌集不來,將就了。
紀秀道:「寬老闆,太客氣了,這麼好的菜,我媽從來沒這麼做過!」
寬老闆道:「南方菜複雜點,北方簡單一些。咱這菜不成套,有南邊也有北邊的。不知合不合口味。」黨林道:「好吃得很。你說北方菜簡單,我們夏陽的才簡單,連鄰縣也笑話我們呢。」寬老闆道:「你們夏陽話有特點,怎麼,飯食也和別處不同?——紀秀,說說那個張武找你媽的事,怎樣?」黨林道:「最好最好。」說着,寬夫人端來一碟菜。寬老闆道:「這是炒蝦仁。哎,紀秀,你說你的。」
紀秀道:「我先說聽我媽說的。我爺爺帶着我爹幫着守城那會兒,太守要我爺爺給守城的年輕人教武藝。我爺爺給我爹說:『上城的人年輕力壯,血氣方剛,但大多沒有弄過刀槍,只宜教他們長刀用法。我琢磨過戚將軍的刀譜,那都是和倭寇對陣中總結出來的,管用。但戚家刀仍嫌複雜,短時間難學出眉目。我簡化了一下,起了個名叫五刀五步。五刀是埋頭刀、劈面刀、刺胸刀、攔腰刀、斜削刀,五步是跨步、插步、弓步、蹲步、鴛鴦步。我又琢磨着將長刀刀頭改作劍頭,要讓長刀還可作劍刺,所以才有了刺胸刀。已經讓鐵匠改了幾把。我先教你,你一天就能熟練。什麼叫熟練?一種刀勢使出後能連帶出其他任何一種刀勢,一種步伐邁出後能變成其他任何一種步伐。你再選上三十個有些基礎的教,以七天為期。再由這三十個推廣開去。』聽說張獻忠第三次打南陽城時,我爹操練的那些人可管了用。這張武就是第一批三十人中的一位。——寬夫人,我們在這兒閒叨叨,讓你忙活!」
寬老闆道:「這是炒苦瓜,苦點,但敗火。黨掌柜,是不是你們那兒沒有?開始吃都不太習慣。紀秀,你說你說。」
紀秀道:「張武只比我爹小兩歲,還和我爹一個名,卻對我爹敬重得很,練武也勤奮。練武以外,總跟在身邊。李闖攻城那次,來的人實在太多,城周圍靠滿了雲梯,好多亂兵爬上了城牆。我爹勸不退我爺爺,便先回家送走我媽和我,又回到城上喝走張武他們,最終和我爺爺被射死在城頭上。」說到爹和爺爺,紀秀語氣仍很平靜,但停下後,眼眶裡溢滿了淚水。寬夫人端來最後一盤山藥炒肉片,靜靜地站在一旁,沒往桌子上放,只怕打擾了紀秀說話。
紀秀猛然注意到端着菜站在邊上的寬夫人,邊站起來邊用衣袖抹着眼淚邊說:「不好意思,讓你忙着做菜,還讓你這麼端着站着。」
寬夫人道:「我一天閒得很,你們能來,我好高興。你說的又這麼感人,我一點兒都不覺得累。真的!」
寬老闆接過菜,對夫人道:「你也坐下一塊吃。——紀秀,你說你說。」
紀秀道:「張武不是勤奮嗎,跟着我爹,還學了我家棍法,黨林哥知道,我弟弟一天練的就是這棍法。南陽安定下來以後,張武便收了一些徒弟,只教棍法。他怕教五刀五步鬧出人命。他的徒弟便占住幾個碼頭,收些保護費,養活自己也孝敬他。」
寬老闆道:「學了你家功夫,沒學你家人品。」
紀秀道:「就是。他找到我媽,叫過師娘,行過禮,就問,你教沒教過黨林這個人,我就奇怪,你怎麼會教一個老陝徒弟。我媽反問,怎麼回事?他說,你教過的話,我給他賠禮,你沒教過,我要和他見個高低。我媽又問,你和黨林什麼過節?他說,我黨林哥不交錢還打人。我媽又問,不交什麼錢?他說,碼頭費嘛。我媽說,你說詳細點。他就說了他的徒弟追加錢時被趕了出來,徒弟拉他前去撐腰,砸了黨林哥幾個瓦罐,黨林哥竟和他們打了起來。我媽這才說,黨林不是我徒弟,是我朋友是我兄弟叫我姐呢!我正在跟前,便插了一句,叫三娘姐呢。我媽訓斥道,你都做的什麼事嗎,還爭強鬥勝!」
寬老闆道:「他還藏着噎着,他就沒說黨掌柜是在我的地界兒蓋得房子。我早就按地塊大小給過他錢了。」
紀秀道:「還有這事!就那,我媽重重訓了他一頓,要他給黨林哥賠禮賠損失。我媽說,和黨林哥見高低,沒他的便宜,說黨林哥的鞭頭,掄一下就能撂倒一個。我媽不讓他以後再說他學的是我家功夫,嫌丟人。他給我媽賠了好多不是,讓我媽原諒他,讓我媽看着他給黨林哥賠禮,後來都跪了下來。我媽最後還是點了頭,只是她太忙,就打發我過來了。」
黨林覺得已聽清眉目,道:「寬老闆,出去一下好嗎?」寬老闆道:「啥事?這兒不能說?」邊說邊跟黨林來到外邊。黨林道:「天不早了,紀秀跑了這麼遠路,讓她跟寬夫人住一宿行嗎?」寬老闆道:「我還以為什麼大不了的,怎麼不行?」黨林道:「人家一個大姑娘家,為咱的事跑出來,我得操心,對吧?」寬老闆道:「我看這紀大姑娘對你親熱得很,一口一個黨林哥。」黨林壓低聲搖着手道:「以前不這樣,一起呆的半個多月從來沒有這麼叫過。這事可不能亂說。我有家口,你知道!」寬老闆笑道:「不說不說。」
回來坐下,寬夫人正問紀秀多大了,定親沒有。紀秀紅了臉搖着頭。寬老闆避開這個話題:「再吃再吃。」黨林道:「好了好了。——紀秀,今晚你隨寬夫人歇息,」又對寬夫人道,「做菜忙了你一通,還得你收拾,又要你招呼紀秀,太麻煩你了。」紀秀道:「天早着呢,我去黨林哥那邊坐坐。寬夫人,本來我該幫你收拾,你看,這——」寬夫人道:「你是貴客,怎能要你收拾呢?你去你去。」紀秀道:「那我去了。」邊說邊起身與黨林走了。
黨林牽了驢,來到碼頭北邊,把韁繩盤在驢脖子上,任驢自去吃河邊的草,自己和紀秀就地坐了下來。眉月斜照,不那麼亮,星星就特別得多,銀河寬寬窄窄橫亘在天穹之上,一直逶迤到了天地相接那兒;清風吹着,送來涼爽,也吹得葉子們沙沙作響,吹得閃着微光的水波波幅大了,吹得白河中或快或慢移動着的漁火微微晃動。驢子噌噌地吃着草,聲兒特別地響,偶爾還舒服得昂頭長鳴一聲,這反而襯得這夜色下碼頭更加寂靜了
紀秀首先打破了沉寂:「黨林哥,咱一塊兒做鏢局吧。」
黨林笑了笑道:「你看,我這人,光問了我的事,鏢局現在怎樣了?」
紀秀哼了聲道:「還記得問鏢局。告訴你,不怎麼樣!」
黨林驚問:「鏢局怎麼啦?」
紀秀道:「不怎麼啦!」
黨林追問:「到底怎麼啦嗎?你倒是說呀!」
紀秀道:「整天給人回話。」
黨林道:「回什麼話?」
紀秀聲兒大了起來:「回什麼話?找的人太多,都先付錢,咱不敢收,沒人押鏢。只挑近處的接,只能接三成客戶。連宗老闆找都沒敢接!」
「哦,是這樣。」黨林長鬆了口氣。
紀秀憤憤地道:「怎麼?你覺得沒事?」
黨林道:「是——不——你看,有人找是好事嘛;人手缺,慢慢就多了。對不?」
紀秀又哼了一聲:「不對!看上的請不去,看不上的找上門來的倒不少!」
黨林岔開話頭:「朝升號離你們鏢局多遠,宗師傅那邊怎樣?」
紀秀停了好一會兒不回答。
黨林道:「累了?噢,也該歇息了。」
紀秀咬了咬牙,重重地道:「不累!怎麼就是『你們鏢局』?人家一聽到你的事,急得就趕過來,剛才聽說你在雜貨市受擠對時,替你擔心死了。可你一說就是『你們鏢局』!怎麼就是『你們鏢局』?朝升號離鏢局不遠,只隔一條街。宗師傅好着呢,隔三差五就給鏢局送些吃的,都比我媽做的好吃。只是老讓那個宗三來送,穿得像個掌柜的樣,酸死了,磨磨唧唧不就走。那天,張武走時,宗三也來了,聽說我來賈營,也要來。煩死人了!」
黨林哪裡經過紀秀這麼訓斥埋怨傾訴過,一下子不知該怎麼應對,啞了好一陣子,才想出一句玩笑話:「這麼大了,還老說媽做的飯不好吃,丟不丟人?」
紀秀答不上來,氣得站起來又哼了一聲:「我累了。」黨林趕緊也站了起來,拉了驢,送紀秀去休息。
寬老闆寬夫人迎了出來,寬夫人領紀秀進去擦洗歇息,寬老闆隨黨林來到雜貨鋪。黨林道:「我這地方太委屈你了。你睡床上,我躺在櫃檯上就行。」寬老闆道:「說什麼呢!我有的是地方。找你說事。」黨林道:「什麼事?」寬老闆說:「急事,現在就我們兩口子知道。剛剛接到的信,你和紀秀出去不大一會兒。家母病危,要我速歸。」黨林驚道:「嚄!要我幹什麼?」
寬老闆道:「我想來想去,想把木廠託付給你。」黨林道:「怎麼!我雜貨鋪才幹了幾天,還老出事,你這麼大的攤子咋行!不是有掌柜賬房他們嗎?我幫着看住廠子行,我會像看我鋪子一樣守住廠子。再說,張武他們不會再生事了。」
寬老闆道:「我信,就是因為信你,才想把廠子託付你。你只要守住這攤子就行。給你交個底吧,他們人倒也精明,可我覺得光有精明不行。你只說成不?」黨林道:「你把話都說到這份兒上,我能說什麼?」
寬老闆道:「不說就不說,事情就這麼定了。大事你拿;大批出貨,大宗銀子出手,都由你簽字畫押。明兒讓他們盤點一下,我給你個底兒。小事有規程,由他們去做。」
第二天一早,寬夫人早早做好了早點,黨林已候在門外,與寬老闆說着什麼。等紀秀梳洗出來,黨林悄聲對她說了寬老闆的事兒,說他要為寬老闆守這個攤子,算是對她一再請求的明確交待。寬老闆在邊上不停地點着頭。紀秀聽了很是驚訝,但驚訝的不是黨林不去鏢局,而是寬老闆老母病危的消息。看到黨林昨晚的態度,紀秀當時就知道他不會去鏢局。
吃罷早點,紀秀便與寬老闆夫婦告辭。她嫌船走上水慢,也想讓黨林多送點路吧,徑直朝沿河北去的大道走去。黨林送了很遠,兩人都不說話。紀秀突然不走了。黨林知道要自己回去,就摸出張武那十兩銀子讓紀秀拿上。紀秀惡狠狠地瞪着黨林不接。那意思再明白不過:你這是幹什麼!
黨林道:「不是給你的,是給咱鏢局的。你應該知道,鏢局剛開張,花用的銀子可不比我開雜貨鋪。以後,不論生意怎樣,我都會把鏢局當做自己的鏢局。」紀秀接了銀子,仍沒有說話,就轉身走了。
望着怏怏不舍逐漸遠去的紀秀,都已看不見人了,可紀秀腰間那綹紅綢仍在眼前晃動,突然,黨林心裡產生了離家時有過的那種感情,他情知不該有,卻揮之不去。只是回到木廠後,很快就被忙碌衝掉了,他已顧不得開鋪子門,便一頭鑽到龐大而又陌生的木頭堆里去了。
第十三章 隴中之行
法王廟會時,憑着二十多年積聚的熱情,憑着近十年的安穩日子,憑着地頭上長着的,綠油油勢頭很旺高到半腿的麥苗,人們很是盡了一番興致。只是會後,從那場幾輩子都難遇到的怪雨算起,直到立夏,也沒有下過一場像樣的雨。眼見着麥子揚花了,要麼撒上幾點,要麼只是淋濕地皮就打住了。到小滿到芒種,仍沒有一丁點兒有用的雨。滿地里密密的青干灰黃的麥子,收割它,幾個人忙活一天,碾打出來,還掙不夠飯錢;不收它,哪天下了透雨,怎麼種秋呀?
一過大年,甄宏祚就全力解決河崖崩塌地還要繳納國課的事。他報呈州里,被打了回來;報呈省里,被打了回來;報呈陝甘總督府,批轉要他自己面呈聖上。他把這個批覆當做真話,積極準備進京面聖。眼見着天氣變成這樣,一般人家吃飯都會遇到問題,河崖十八村無地還得納糧的家戶,日子怎麼過?
就在他要啟程的先一天,總督府發來一封加急公文,要他帶着寫好的奏章,親自來蘭州一趟。該不會是總督變了主意吧?要是換着法阻擋自己呢?夏陽在蘭州去北京的南道當腰上,趕到了蘭州,北京也到了;如果先讓去蘭州再去北京,就是跑了兩趟北京。這不是要命嗎!但是,官大一級壓死人,別說大了好幾級呢!
甄縣令帶了戶房師爺和同副捕頭當日啟程,改赴蘭州。一路上免不了起早摸黑,風餐露宿。緊走慢走,花了二十餘日,才趕到地兒。擦黑擺渡過了黃河,二更天,總算來到這圍在萬山之中,踞於黃河之濱的赫赫有名的陝甘總督衙門前。認了門,就近尋了旅店,填了肚子,已過了三更。未曾脫衣,才蜷曲一會兒,怎麼天就亮了。便又急急去了衙門,但衙門緊閉。等了半個時辰,待到應卯的官員陸續來到,門才開啟。
甄縣令遞上名帖。門子仔細看過,又端詳了來人,方道:「你就是陝西夏陽正堂甄宏祚,你可真有名氣啊,總督府里掛上號了。那年,給你布政使你不做,現今,做個七品官要和聖旨較勁。真有你的!總督就你的事專有交待。帶你的奏章沒有?——帶了就好,請把副本留下,總督要看。別怕,我會給你收執的。還有,何處落腳?」
就這麼,堂堂縣令只在總督衙門門子跟前打了個到,往後一連三日,一日兩次,每次都吃閉門羹。不只不見,怪事還不斷。當天從衙門往回走,便有人盯上了。半夜,忽然來了幾個公人敲開店門核查身份。第二天,又有公人要求店主騰空所有房間,說有貴客要來,趕他們走。第三天,新店的主人說,收留了他們,老有人找麻煩。
同欣不解地問:「總督衙門重地,怎麼住店都不能安生?」
戶房師爺答:「這是為難咱們呢。」
「為什麼為難我們?」
「你問大人。」
同欣催道:「大人,你說呀!」
甄宏祚答:「要咱們知難而退呢。」
「誰呀?」
戶房師爺卻道:「這還要說?大人,這見又不見,走不能走。怎麼辦?」
甄宏祚道:「當然不能總這麼待着,等不起呀。明天我再試試。」
兩人點着頭,同欣還醒悟地加了一句:「我知道了,我真笨。」
第四天,甄宏祚混在應卯官員中,不理門子,硬往裡闖。門子拉住不放。甄宏祚喊道:「夏陽正堂甄宏祚求見總督!總督大人讓來,門子卻一味阻攔,是何道理!」同行官吏,面面相覷,不知所以。這麼喊了幾句,裡邊就傳出了回聲:「放他進來!」
點卯後,總督放下預定議程,正襟高坐,威嚴地道:「堂下可是夏陽縣令甄宏祚?覲見本督,緣何不跪?」
甄大人上前跪道:「下官甄宏祚,拜見總督大人。」
總督斥問:「區區七品縣令,緣何咆哮總督衙門?」
甄大人辯道:「甄某不敢無禮。只因總督令下官前來,卻幾日受門子阻止;所歇小店,還屢受騷擾。下官以為,這斷不會是總督指令。方才高聲,只為擺脫門子,以便參見總督大人。」
總督換了口氣:「陝甘轄區戰事早熄,風調雨順,民生康樂,已有聖旨通報嘉獎。怎麼你這個夏陽縣令偏偏多事。是想給聖上增添煩惱,還是想給本督添亂?」
甄大人道:「陝甘一帶社會安定,民生康樂,夏陽也是這種情形,所以去今兩年,老百姓自己搞起大型社火,慶祝盛世。這當然是聖上聖明,也是總督大人治理有方。但轄區廣闊,人情有異,地理不一,風雨難同。比如在下來日,西安以東渭北各縣,旱情已經昭顯,而隴山腳下,陰陽協調,豐收在望。如此可知,事情常有意外。」
總督責問:「駝生北漠,難免饑渴,牛產南國,多蒙水澤。地理不同,情狀有異。怎麼來求公平?」
甄大人回道:「事情難以盡平,但明主力求公平。所以聖君田分九等,賦稅有別。所以古人說:可平者,平之為賢;不能平者,平之為聖。願大人求賢求聖!」
總督頓了頓:「本督日理萬機,為夏陽一事已頗費心神,你應知分寸,讓本督省心,為聖上分憂。」
甄大人道:「在下所為,正是為聖上分憂。家國一體,為民就是為君。願大人明察。」
總督耐不住性子了:「我讓你進京面聖,意在難為你阻擋你。你卻不知天高地厚,以七品微員,要去和聖上辯理。古今豈有此理!」
甄大人只道:「天高催人效忠,地厚只為載民。」
總督終於惱怒爆發,陡然喝道:「堂下各位,仔細聽聽,本督何曾對一縣令費此口舌。杖責二十!」
甄大人喊道:「下官不知何罪?」
堂下一片愕然,愕然於總督的暴怒和責罰,也愕然於這位小小七品微員的無畏無懼。
衙役頗感突然,呆立堂下,無人動手。
總督氣得放了粗口,喝道:「耳朵都用驢毛塞住啦!摘去頂戴,當堂杖責!」
一衙役先上去摘頂戴,甄大人拼死護住,兩衙役又過來一人拉扯一臂。甄大人高喊:「頂戴聖上所賜,不得造次!」但任憑他怎樣掙扎,頂戴還是被摘了去,人也被扳倒在地,挨開板子。堂上靜悄悄的,只聽得夾在一片出氣聲中的重重的板子聲和計數聲。
一,二,三……
板子聲終於停了,衙役的計數聲也終於停了,在場人等懸着的心總算落了下來。總督的氣兒盡情地出了一通,雖仍努力彰顯威嚴卻明顯和緩地問道:「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甄大人想爬起來,手腳卻不聽指揮,只能抬起頭,低沉但清晰地答道:「忠君憂民,雖死猶存!」滿堂上下,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這一來可真堵得總督半天說不出話來,但事到如今,總得有個交待呀,終於,只聽見他有氣無力地道:「明天給我回去。」又朝外擺擺手,讓眾官散去。他已沒有心力進行預定的議程了。
認出兩個衙役連攙帶拖的是縣令大人,戶房師爺和同欣驚呆了。同欣抓住一個衙役的胳膊喝問:「怎麼回事?」那衙役疼得咧着嘴道:「總督大人他……」戶房師爺拉開同欣的手,示意背上甄大人趕緊離開,又回頭對被抓的衙役連連點頭示謙。
趕到住所,跟着進來兩個人,一個自稱總督衙門的,來送甄大人的官帽,一個大夫模樣,背着青囊。放下甄大人,同欣轉過身來,怒對來人,抓起桌子上的茶壺,一把捏成碎片,厲聲道:「如此對待我們只知百姓、從無自己的大人,不怕天譴嗎!」
自稱總督衙門的一位急道:「官員們都背着總督翹拇指呢。總督也派來大夫。看傷要緊。」
同欣卻道:「我先拍你一掌,再讓大夫瞧瞧?」嚇得這位官員直往後躲。
戶房師爺忙拉開同欣道:「看傷要緊,看傷要緊!」
甄大人也吃力地道:「不得造次。」
臨走,這位官員對送到客店門外的戶房師爺道:「大夫說,傷最少需休養十天,我看,十天以後,你們回去吧。要勸勸你們老爺,別再去總督衙門了,我們這些品級低的說話不算數呀。你們老爺已經盡全力了,再僵到這裡,更不好收拾。」
當天晚上,同欣背人化裝一番,輕移腳步,剛要抽開店門門栓出去,只聽得另住一屋的甄大人喝道:「哪裡去?」同欣停住腳步。
又是一聲:「到我這兒來!」
同欣尚未進甄大人屋門。又是一聲:「脫下你那身行頭。」
同欣換過服裝,來到甄大人床前。又是一聲:「今晚陪我歇息!」
同欣道:「我氣不過,我要報仇!」
甄大人道:「胡說!俠客也不是這麼做的!明早我們回去。」
同欣道:「大人,你這傷!」
甄大人強調道:「你倆商量一下,明早我們回去!」
同欣和戶房師爺打算雇用馱轎。人傷成這樣,馬騎不成了,僱車不說費用大,顛簸得也不行。但甄大人不同意:「讓馬空走,花錢雇轎,這不行。你們不知道李廣的故事?」李廣傷病遭俘,躺臥在兩馬之間繩索編制的網絡里,被押往敵營,途中又偷空兒逃脫的故事,兩人都知道,只是縣令大人的體格既不能和李將軍相比,千里迢迢的歸程也不能和短暫的押程相比呀。但縣令大人執意拒用馱轎,戶房師爺只好連夜上街尋找繩索和木杆了。甄宏祚不讓同欣出去,他怕同欣管不住自己。
遵照縣令大人吩咐,三人第二天早晨踏上歸途。同欣牽馬在前邊走着,戶房師爺騎馬在後邊跟着。當中的甄宏祚,實在不好受;雖說戶房師爺在繩絡中間放了塊木板,讓甄大人受傷的臀部顛簸小了一些,但沒多久,縣令便臉上沁滿汗珠,只是一聲不吭。兩人也不好說什麼,只能默默地揪心。
中午,在路邊一家小店填了肚皮,餵了馬,隨即起程。耽擱不起時間,天黑前還要趕到下一站呢。行走間,無意發現兩個人騎馬追來,待至跟前,竟是昨日來過旅店的那兩位。大家不由一怔,相互看看,又不知該說什麼。那位官員責問戶房師爺:「不是給你交待過嗎,這傷怎能上路?還就這麼趴着!」那大夫道:「這樣趴着,繩絡擺着,瘡痂結不住,傷怎麼好?」
戶房師爺將那官員拉到一邊,低聲道:「甄大人執意要走,我們下人有什麼辦法?這原因甄大人不說我也知道,錢我管着嘛。我們盤纏是按天算的,在蘭州閒住了幾日,甄大人就有些焦急,沒想到事情又從這兒來了。我們讓坐馱轎,甄大人堅決不用。平日衙門裡邊,一文錢恨不得掰兩半用,他怎麼捨得坐兩千里馱轎?」
那官員正色道:「趕緊把人放下來,看傷換藥。馱轎後邊就來,錢付過了。」
戶房師爺仍低着聲:「謝謝大人。這樣,我的日子就能過了。」
趴在馱轎里,雖說轎身仍然擺着,但轎底平整,木板做的,傷口不受影響,又有大夫留下的藥,按吩咐的時間換着,瘡口也就日漸好了起來。瘀血化去,雖需時日,已不像創傷那麼緊迫了。這天,透過轎窗,看着兩邊景色,想着一個多月來的事情。甄宏祚不禁浮想聯翩,隨口吟道:
其一
星夜啟征程,如焚西赴隴。
河神奪地肆,旱魅毀稼橫。
滴雨面容爽,點頭麥穗迎。
策驅入沓嶺,山綠馬蹄輕。
其二
隴下田頭鬧,天開送惠風。
汗滴心裡醉,鐮動笑中行。
回首金城阻,搖頭督署爭。
辱身情不補,何以對生靈?
吟罷,他苦笑着,將前一首名為《前往》,後一首名為《歸來》,合稱《隴中行》。
不能就此打住,他想,不能你讓面聖才去面聖,你不讓進京就不進京了。坐着馱轎正好養傷,傷養好了還要進京;不然,不說縣衙說話不再管用,不說給夏陽父老無法交待,首先平復不了自己的心。
第十四章 專理木廠
玉米早收了,麥苗已經顯出行來,正趁着分櫱前的機會個管個地比誰長得快。棉花葉子蔫了,盛開的骨朵陽光下連成一片,分外耀眼。賈營的白河,無論南望還是北望,都格外地寬,河水銀亮銀亮地瀰漫開去,像是想和棉田連畔。河中的船,單個時,就如未能連在一起的棉骨朵間的空兒;連成了串,又如棉田間的麥田。碼頭上上下下忙碌着的,不停地用手指刮着汗水甩着汗水的腳夫,光着膀子,扛着,抬着,卸載着船上的木料。日頭斜掛西天,照射着橫掛在檐前的,紅底黑字的「黨記雜貨」大招子,讓招子分外搶眼;卻曬得轉到櫃檯前面,望着碼頭想着木廠的黨林有些眼花,明明覺得有人朝自己跑來,就是分辨不清。而此時,只聽到一聲久違的呼喊:「黨老闆!」
來人是阿牛。搭乘的南下的船,尚未停穩,他便跳上岸來,邊喊邊跑向黨林。黨林也喊着「阿牛」,迎了過去。又拉着阿牛,來到鋪號後邊的陰涼處。驢子見阿牛來了,也又叫又踏又晃又甩地表示歡迎。
阿牛邊喝水邊四下看着邊說了起來,不知是激動還是這幾個月曆練得,一點也看不出原來的木訥了:「怎麼就巧,剛進南陽城,就遇見了給咱送鹽的那個領班,我問你的情況。他說:『好着呢,還在賈營。』我不信:『還在賈營?』他說:『比原來還好找,坐着船,遠遠就能望見。』近了一看,真是這樣。鹽領班還帶我見了宗師傅。他先問我:『想不想知道為啥讓你們老闆包了賈營一片的鹽務?』我說:『想呀。』他說:『帶你見個人,是他介紹的,順道。是位大老闆,姓宗,不僅介紹還兼保人呢。』宗師傅可真是老闆的樣,抬腳動步,衣着說話,越看越像大老闆。哦,人家就是大老闆嘛。」
黨林靜靜地看着阿牛一個人不停地說着,有驚訝,有喜悅,有慶幸。直到阿牛頓住了,才問道:「四個多月了,都在哪兒?」
阿牛摸摸下巴:「唉,跑的地方多了,求的人也多,卻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活路。最早在瓦店人市上呆過幾天,被蓋房的叫去做小工,混飯還行,就覺得不是常乾的活兒。又當了一陣子縴夫,跑了一趟襄陽,算開了眼界,但那個累呀,趕回到南陽,領了工錢,就辭了。還幫人收過莊稼,跑了這家跑那家,忙時沒黑沒明,忙後又要另找行當。乾脆回了趟家,我媽見我可高興了,直說帶回來的錢不少,實際上給家裡留下的,都是你給我的錢。跑來跑去賺下的,要麼隨手用了,要麼踩踏到路上。跑慣了,家裡待不住,沒住半個月,我又出來了。先到了石橋,石橋當然熱鬧,可熱鬧的是人家,轉來轉去,就是沒有自己的地兒,這才坐船來到南陽。你說巧不,怎麼就見了鹽領班?哎,老闆,二毛怎麼走的?我在南陽城裡還見了二毛,和鹽領班分手後在去碼頭的路上,像是剛從碼頭過來。他說他早都不在賈營幹了,和我一樣,一直再也沒有遇到位靠實的老闆。我說,我打聽到黨老闆了,一起還跟黨老闆干吧?他搖了搖頭,沒有說話,就走了。你說怪不?」
黨林正饒有興趣地聽阿牛講自己的故事,沒想到突然扯出了二毛,興致一下冷淡下來。阿牛看出黨林神色的變化,問道:「老闆,二毛怎麼啦?」
黨林平靜地答道:「也沒什麼。你走那天,下午他就走了,只是沒給我招呼一聲。早知他走,就不該放你走。不說他,說你。」
阿牛道:「我都說完了嘛,該你了。我看你的故事多着呢,你和宗大老闆的故事,你這幾個來月的故事,肯定比我多,比我的好聽。」
黨林道:「宗老闆是我師傅,細說,話就多了。今兒先放到這裡。我這幾個月也還順當也還熱鬧,都以後說吧,眼下顧不得。眼下要緊的是,我還代管着這個木廠,忙得顧不過來,正盼着你哪天回來幫我呢。找個人?找個人倒容易,不稱手呀。哎,你就來了。」說話間,天不知不覺就不早了,驢子叫起來了。黨林道,「嫌把它撂一邊了,你餵一下,我給咱們叫飯,邊吃邊說。」
就這當兒,民信局信使送來封書信。民信局明代就有,做的是遞送民間包裹信件生意,南陽水陸碼頭,早幾年已經恢復了。黨林對阿牛說:「寬老闆的,就是這木廠老闆的信。」讓先招呼信使坐下喝水,自己趕緊開封細讀:
黨掌柜黨老弟:
見信如唔。母病未安,一時難返。尚需勞累賢弟。
木廠託付於汝,實乃吾之幸運。應是上天安排:讓你遭受磨難,與我相識;要你經歷逼迫,讓吾知汝。使吾遇困之時,能將木廠托汝,放心返鄉侍母。
所託之事,難在與掌柜相處。汝現今應知託付於汝之原因。李掌柜人也聰明,但貌相陰,性亦陰。開廠之初,雖幫余不少,而一旦握掌柜之柄,即生架空吾之意。余原欲辭退,只因尚無人選,無奈留患於汝。今日當已為難於汝。不得已,可辭去,由賢弟定奪。
二夫人囑吾提說紀秀,言紀秀有意於汝。吾閱人眾矣,而觀紀秀,人品才氣容貌,可配賢弟。二夫人原從吾已知賢弟家有妻室,說她言之紀秀,紀秀唯不語而已。吾娶二夫人,本大夫人之意,說她需在家撫幼奉老,難以隨從,如此,則兩相心安,既免猜忌,又少誘惑。
又,吾歸時,汝囑吾多帶銀兩,言富路窮家,可免受困於途,且治病費重,萬一不測,更需花銷。賢弟不必擔心。途中銀兩綽綽有餘,家中存銀亦足用矣。三年五載,無需顧慮。
順致
平安
愚兄寬某
順治十七年七月既望
黨林雖寫不出這麼文縐縐的句子,但意思看得過來。他問過信使回複方式、資費數目,然後說:「我這就去外邊叫飯,你吃飯,我寫幾句回信如何?」信使道:「天不早了,我坐的船今兒晚上歇瓦店。你趕緊寫吧,不然,我等不及了。」黨林沒再說話,翻開賬本,撕下一頁。毛筆墨盒現成,不是天天記賬嘛。他提筆寫道:
寬老闆:
來信仔細看了。請放心在家伺候伯母,我一定盡心守護木廠。
黨林年月日
又向信使買了封套,照着寬老闆信套寫了郵址,裝好封好,付了資費,將人送到船上。黨林看信寫信時,阿牛已捅旺爐子,餵了驢子,又做好拌湯,擇洗好了廚下現放着的豆角萵筍九月韭。趕他回來,還炒出兩個菜來。面對黨林的詫異,阿牛說:「這次回家,我給我媽說,都是小伙子,怎麼人家二毛就會做飯,我只能刷鍋。我媽說我省事了,說學做生意的,都要學會做飯呢,就教了我幾樣簡單飯菜。老闆,你嘗嘗,看味兒怪不?」
黨林一邊吃着,一邊說好,一邊腦子不由分說地跑到寬老闆的信裡邊去了。看來寬老闆一時半會來不了了。提說紀秀,什麼話嗎?眼下要做的就是木廠的事。讓寬老闆說了個正着,三四個月了,說是自己拿木廠的大事,可木廠的事兒不論大小,自己好像一點也管不上。就沒有大批出過貨,簽什麼字?大宗銀子雖動用過,但不是廠里進貨,廠里就不需要進貨,人家借用,過後也都還了。廠里幾乎沒有盈利,發工錢都要老本貼補。眼見着碼頭上出出進進的木頭,卻都是別人家的生意。賈營最大的木廠,咋就經營到這個份上?剛接手時,花老大勁熟悉的木料品種、進出價錢、買賣方式、僱工類別、工錢差異這些經營木廠的學問,至今一點兒也沒用上。
阿牛見黨林像是發呆,夾起菜好一陣兒不往口裡送,嘴也不說,眼也無光,忍不住問道:「老闆,怎麼啦?你吃呀!」
黨林像是回過神來,撲哧一聲笑了,道:「沒,沒什麼。我想寬老闆的信。吃,都吃。」
晚上睡下,黨林仍在想着寬老闆的信。阿牛的到來,讓他能靜下心來思考木廠了。雜貨行情阿牛熟悉,貨鋪買夫好多阿牛熟悉,送貨客商好多阿牛熟悉。就這麼個鋪子,不再倒騰,阿牛一人對付得了,該是自己全力應付木廠的時候了。由着木廠這麼下去,不要說對不起寬老闆,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師傅讓自己從「小」做起,到頭還不是為了一個「大」字?眼下說不定是個機會,誰捨得撂下這麼大個攤子讓咱整治?整好了木廠,從學生意講,應該是越過了好幾道坎呢。
哎,盡想美事了,要緊的是眼下怎麼辦?總不能直接找掌柜說人家不對吧。如果讓人家問住敗下陣來怎麼辦?找夥計了解,找那個夥計?夥計在掌柜手下找飯吃,時間長了,依賴大,能給一個臨時照看木廠的人說什麼?哦,寬老闆信中沒有說到賬房,賬房會不會還信得過?看來,得先找賬房試試。如找賬房,就先要賬房相信自己。這下明天有事做了。
理清了頭緒,黨林的覺特別香。趕醒來,天都大亮了,阿牛已經卸下板門,做好了飯。黨林讓阿牛一塊坐下,邊吃邊說:「吃過飯,你把貨和賬對一下,心裡有個底。從今兒起,鋪里進出貨物你都操上心。寬老闆回來之前,我得照看木廠去。聽清沒有?」
阿牛愣了一下,摸摸下巴,說:「聽倒聽清了,可我沒操過這麼大的心,我做不來。」
「什麼做來做不來,操上心就行!我不還在嗎?」
「我一定會用心做鋪子裡的事,連帶做飯,餵驢子。但做好做不好生意,真不敢說。老闆,你要買菜,還有,你該不會睡到木廠那邊去?」
「心還滿細。我就是要在寬老闆外屋住幾天。飯回來吃。菜我買,你沒時間幹這個。」
「一看陣勢就知道廠子大小,出出進進十幾號人,咱一個生人單另住着,不熟悉人家,怎能管好廠子?」
「好,好了好了,就這樣了。」
賬房獨自一屋。黨林見了賬房先生,招呼道:「先生好。」還是寬老闆走時,把木廠所有雇員叫到一起,賬房算是和臨時代理黨林也打過一次招呼,但從此,再也沒說過話,黨林還不知人家姓什麼。
賬房站了起來,不冷不熱地回道:「黨老闆好。」竟然連一句「你請坐」的敷衍也沒有。
「三四個月了,沒來看望過先生,至今不知先生貴姓,真不應該。」
「不必這樣。寬老闆交待得清楚,大筆進貨出銀你說了算,其他按老規程來。一般買賣不就是李掌柜說了算嗎?你沒有什麼不對,我怎能承受起你這樣的話!」
黨林覺得挺尷尬。沒讓自己坐,人家又站了起來,這是讓自己走,還是以為自己只是來轉一下本不準備坐呢?看來先得自己說清。便道:「咱們不能都這麼站着說吧,你請坐。」
賬房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你是客人,你請坐。」
黨林一邊落座一邊道:「先生貴姓?」
賬房一邊倒茶一邊答:「免貴,姓劉。木廠只有我年紀大,就叫我老劉吧,他們都這麼叫我。」
黨林道:「這麼叫不夠敬重,但親近。好,只當着你,我也這麼叫,但當着眾人,還是稱呼劉先生好。哎,老劉,你說咱們木廠生意怎樣?」
聽着前半截話,賬房覺得還挺舒服,趕聽到後半句,心裡剛鬆弛開的弦又繃緊了,他苦笑一聲,只盯着黨林,卻不答話。
「不好說?不宜說?沒頭說?別太認真了,隨便說說嘛。」
「你不是天天盯着碼頭嗎?碼頭那麼紅火,咱掙下的卻不夠開工錢。就這,還不算給你的錢呢。你能看不出問題?」
「我是外行,對廠里又生,只覺得不對勁,但不知道哪塊兒不對勁。」
「哎,你臨時代理幾天,趟這渾水幹嗎?寬老闆在時就沒理順呀。」
「不相信我?怕說出想法,我又管不了,或者不願意管,反給自己惹麻煩。對不對?」
劉先生不答話,不點頭,也不搖頭,只盯着黨林微微笑着。
黨林雖感不到真誠,但也感不到隔閡,就覺得是時候了,便拿出寬老闆的信遞給賬房。
劉先生見是寬老闆的信,忙站起來接住,又從微微點頭的黨林眼中,看到了一種信任。他先去閉住屋門,才坐下讀了起來。劉先生邊讀邊想,這個臨時代理已經丟掉了「臨時」兩字,受到了老闆莫大信任,掌握了任免雇員的權力,雖已決心開刀,但不慌亂,而是先摸情況,尋找依靠力量呢,入門。自己當然希望木廠好了,當然知道問題在掌柜身上,當然願意幫助黨代理了。只是掌柜整日勾着鼻子沉着臉,掌管木廠好幾個年頭了,內內外外交往又多,由一個不了解內情的代理解僱,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自己空說難得到重視,輕率又顯得毛糙。他正思量如何表態的時候,忽然聽得黨林說道:「劉先生,哎,老劉,有沒有其他想法,比如說,另謀高就?」
「噢,年紀不饒人,苦力不行了。好在還能寫寫算算。就盼望廠里好,自己沾沾光。這兒離家又近。哪想過什麼另謀高就?」
「那咱們就能想到一塊兒。」
劉先生突然覺得,眼前這個人比他的年齡穩當得多,態度還是明朗一點好,就一邊把信遞給黨林一邊道:「寬老闆把對了脈,不僅找對了黨老闆,也看準了木廠的癥結。我會幫黨老闆的。只是,帳面上抓不住什麼,要另想辦法。」
趕從劉先生屋裡出來,黨林才覺得肚子餓了,抬頭一看,早過了吃飯時辰,只覺得一個身影遠處閃過,定睛一看,是李掌柜,沒錯。該不會盯了很長時間吧。嗨,盯吧,知道了又有什麼。他這是害怕呀!這麼想着進了鋪子,卻見師傅坐在當間。他大步上前,一邊喊道:「師傅,想你,你就來了!」宗祁也站起迎了過來:「黨老弟,怎麼,又有事了?」兩人同時笑了起來。
阿牛道:「老闆,宗大老闆來好一陣兒了,他一定要等你回來才吃。好了,你們邊吃邊說。」
宗祁道:「我也餓了。這小伙子我那天剛見過一面,怎麼就到你這兒了?」
黨林道:「他叫阿牛,原來就是我的人嘛。我天天都想見到師傅,但我現在還真遇到了大事。正幫寬老闆打理這木廠,問題一大堆,推不動呀。寬老闆幫過咱,人家有事托咱照看,可有力使不上。碼頭上整天木頭來木頭去的,就是不見咱的生意。」
宗祁道:「代管木廠的事我知道,紀秀說的。只是紀秀沒說你還雇了人。你說,木廠怎麼就推不動?」
「寬老闆走了四個多月,掙下的錢還不夠開銷工錢。直到昨天接到寬老闆來信,才知道就是因為掌柜不可靠,才把廠子託付給我。信中又說,他一時來不了,大小事情,都由我辦。不辭了掌柜,事情好不了;真要辭,木廠一直掌柜管着,怎麼辭呀?」
「哦,你是怎麼想的?」
「我想先了解情況,想弄清他一天出來進去忙東忙西在幹什麼。行生人生,早晨去賬房屋裡,沒想到竟坐了這麼久。賬房先生還行。哎,師傅,你剛才怎麼說『又』有事了。不就這事嗎?」
「這事是這事,這事來前我不知道。你說,前一陣兒,紀秀為什麼來賈營?」
「半年不見,我的事你可都知道,在先雜貨市遭擠對,後來與張武一夥幹仗,對吧?我這人運氣好,馱點棉花出門,值不了多少卻招眼得不行,翻秦嶺嚇死人,怎麼就遇到董大哥,吃了住了還換了那麼多好藥材!到雜貨市沒幾天,就包攬了賈營一片鹽務,把雜貨市那些主家眼紅死了。讓雜貨市擠對出來,怎麼就遇上寬老闆,照樣在賈營做雜貨,位置比原來還好。遭幾個小混混敲詐,一再問咱要錢,逼咱動手打架,又有扈三娘讓紀秀來解困。師傅,你說,我這人做生意,運氣是不是好!」黨林笑道。
宗祁也笑道:「好,好!但我就覺得你不像一個出門只為做生意的,你說,我說的對嗎?」
黨林怔了片刻,道:「師傅,你怎麼就覺得我不像一個出門只為做生意的,你說。」
「跑得比我還遠,就為了賣那點兒棉花?」
「師傅,你說對了,也沒存心瞞你,你不是沒問過我嗎?就是阿牛知道也沒什麼。我是躲官司跑出來的。」
「你看,你看,我說對了吧。哎,說來聽聽。」
黨林拍怕腦袋:「按說也沒什麼,可我不敢想這事,一想就頭疼。一伙人要奪我家的山地,圍着拿棍打我,我抓住一根奪了過來,沒想到,拿棍的也隨着過來跌倒在地,頭撞石頭死了。家裡人都說我惹上了人命官司,讓我出來躲。這一躲就快一年了,也不知家裡怎麼樣了。一想這事,我就頭疼死了!」
「別怕。他們持械行兇,咱空手防衛,他們仗勢強取,咱依法墾種。是他自己失手撞死的,咱能擔多大責任?年前生意是旺季,路也不好走。過了年我要回趟老家,順便打聽打聽。」
阿牛道:「老闆,一伙人拿棍打你,還能占了便宜?」
宗祁對着阿牛問:「這都不知道,怎麼還算你們老闆的人?你能沒見你們老闆獨自對付張武一夥嗎?」
阿牛隻是搖頭:「我就知道我們老闆是好人,生意做得好,對我們夥計好。我沒見過我們老闆打架。」
宗祁道:「我可見過。別人都說我劍上功夫好,一比就差遠了。那是真刀真槍打出來的。哎,黨老弟,功夫跟誰學的?」
阿牛道:「邊吃邊說,飯都涼了,要不,我再熱熱?」
「不用不用,邊說邊吃。小伙子,仔細聽着,長見識。」
「教我武功的師傅叫王應朝,是我們鄰村人,去世多年了,我是師傅最小的徒弟,別人叫我關門弟子。王師傅可厲害了。左爺守夏陽時——左爺是前明我們夏陽一位縣令,很得夏陽人愛戴,我們那兒的人都叫他左爺——十萬亂兵來犯夏陽,左爺硬是讓這些人沒有得逞。左爺破格任命王師傅做了千總,王師傅領着一幫弟兄,哪兒緊張衝殺哪兒,從不失手。」
「左縣令固守夏陽我從小聽過,但王應朝師傅的事今兒才聽說。前幾年你們夏陽起兵反抗新朝時,王師傅參加了沒有?」
黨林聽了,神情一下凝重起來,卻道:「阿牛,飯真涼了,拿去熱熱。」
阿牛道:「成,成。老闆,你先歇會兒,馬上熱好,就來。」
黨林道:「想聽好說,以後機會多得是。——王師傅沒有參加,那時,王師傅已經過世,我倒是參加了。」
宗祁詫異地道:「你?就你!那時你多大啊?哎,先別急,等一下阿牛。」
黨林緩了會兒:「那年我十六。起兵的首領姓劉,前明做過巡撫。我舅和劉巡撫同村,我不是學了點武藝嘛,就去投軍。劉巡撫嫌我太小,我報了師傅的名,又演示一通,才收了我,但只安排我做了親兵。劉巡撫最受人敬重了,他變賣家產,用做軍需,文武雙全,愛護士卒。夜裡常為我們幾個年紀小的蓋被子,空閒常和我們這些親兵對練刀槍。最大的那次出擊,幾經衝殺,戰況不利,他下令撤退,自己卻騎馬斷後。有人勸他,主將不能冒這種風險。他說,主將斷後,軍心才穩,部隊才能完整地退下來,趙子龍就這樣帶兵。事敗以後,劉巡撫硬是一個人扛起了責任,救下幾千人。這都是我眼睜睜看到的呀!」說到這兒,黨林眼裡溢出了淚水。
阿牛不解:「一個人怎麼擔起了責任?」
黨林道:「相持時間久了,義軍最終抵擋不住源源不斷前來圍剿的官兵。劉大人見勝利無望,便向對方求和。說義軍全體放下武器,自己接受懲罰,但不可追究其他參與者責任。不然,『玉石皆焚』。這是劉大人原話,就是義軍會抵抗到最後一個人,也要讓對方死很多人。最後,劉大人當着眾人服刑,至死,氣色一點兒都沒有改變。我就在跟前站着。劉大人一直罵我們,讓我們離他遠點,說我們不省事。他是怕我們隨他一塊去死,我們真有過這種打算。」
宗祁道:「壯烈之士!——我一直覺得你和別的人不太一樣,今兒個才知道怎麼回事。」
黨林道:「多年不提這事了,家裡一直不讓給別人說。這是和衙門做對的事呀!現在說起來也都成了閒事。師傅,不說這了,你只說木廠我該咋辦?」
宗祁道:「沒有以往的閒事,眼前就麻煩了;有了以往的閒事,眼前就不難。你跟王師傅練下武功,從劉大人學得仁義。一個人來到這裡,不長時間,就結識了扈三娘、寬老闆、還有我,這些都不能算普通的人緣,都是關鍵時能幫上手的朋友。已經做了半年多生意,有了不少經驗,又能從賬房入手解決問題。我看你就照你想的辦。木頭生意好啊,逃難返鄉的,尋居好地兒的,來做生意的,賣力糊口的,誰不要房住?有舊的,修舊的;沒舊的,蓋新的;蓋不起好的先蓋窩棚,情況好了再蓋房子;發了財,又建華屋。我看這木頭生意好得很,一二十年也消停不下來。我看你將來可以在這一行發展。我看你就照你想的辦,先弄清問題,沒弄清先不捅破,一旦捅破就要讓他服軟走人。哎,阿牛,你老闆的故事先到這兒了,你忙你的去,我有事要和你老闆說。」看着阿牛收拾碗筷走了,宗祁才道:「老半天了,見了我光說你的事,你都沒問我為啥來這兒!」
黨林又拍了下腦袋,不好意思笑了:「人家不是心急嘛。再說,你問我那些事,我能不說嗎?」
宗祁道:「我去瓦店想盤那個綢緞莊,開一個分店。但人家口張得太大,我拿不下。以前我沒來過瓦店,這次,在瓦店轉了一圈,感覺比我們朝邑縣城攤子還大,環城那麼多碼頭。不說這啦。我找你,只是想問你和紀秀的事。」
黨林一聽瞪起了眼,聲兒也大了起來:「我和紀秀怎麼啦?對師傅我不敢說假話。我和紀秀沒什麼呀!我有家有口,還在外躲官司,人家大姑娘,我和人家能有什麼?」
宗祁板起臉,只低着聲兒:「看你說的,像是把你冤枉了。我問你,三娘說,紀秀來賈營時興沖沖的,回去後就整日悶悶不語了。怎麼回事?」
黨林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看出紀秀有些變化,但是,真的,這不關我的事。咱們分手以前,一天黏我,叫我叔,紀秀很少說話,說也不帶稱呼。來賈營時,卻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喊我哥,我也覺得突然。又一再邀我去辦鏢局,我離南陽時她這麼說過,這你知道。她還說她煩宗三老找她。就這些了。」黨林說的都是實話,但沒敢說送紀秀離開時自己心情的變化,他覺得那只是一會會的事,早已過去了,說出來不是多事嗎?
「你就沒說你怎麼惹紀秀生的氣!」
「人家幫我來了,我哪能惹人家呀?我就是想辦法躲人家的話,說我不能去做鏢局。」
「躲官司不是大事,說清了,三娘不會在意。以往在外做生意的,另娶一房的事兒多了,只要三娘她們不嫌棄。這都沒什麼。只說,你對紀秀有沒有意?宗三喜歡紀秀,讓我提親。三娘說,紀秀心在你身上。如果你有意,我便不提宗三的事,如果你無意,我就給宗三提說這事。」
「師傅只管給宗三說。不必說我有家口有官司,只說我祖上,就沒人娶過二房。前明時,我們党家有位先輩叫黨孟輈,和夏陽一位朝里做官的是親家,災荒年間,一次就拿出幾百石糧食救濟災民,財勢多大啊!就他,也沒有娶過二房。我怎能亂了規矩。寬老闆信中也提說這事,這是信,你看吧。讀了信,我只是覺得怎麼能想這事?你挑明了好。師傅,心裡話,紀秀是個好姑娘,但我絕不會娶人家。對師傅不敢說假話!」
一邊聽着,宗祁就看完了信,道:「寬老闆和我看法一樣啊。紀秀不光人好,也挺有眼力。哦,不說這話了。探得你的底話,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記着,過了年,我要回趟老家,我去夏陽把官司打聽清楚。捎什麼得事先準備啊。」
=來源:韓城市党家村景區
=最溫度、最深度,最情懷、最態度的平台
心往韓城,長樂未央;
黃河邊的文史聖城,文明古國的詩意棲居地!
千年隋唐城,多少英雄俱塵土,
唯有這座城,亘古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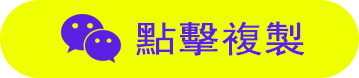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現代年輕人的情感問題很多,需要這樣的情感諮詢師,很專業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