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之星」作品導讀
《空房間》以人物姓名直接為章節命名,並在不斷的交替切換中,通過人物各自的視域締結了中篇小說的結構。小說既敘述了在關係疏離的家庭中,兒子李一凡的自我迷失,也追索了做着兩份工作、獨自撐起生活的母親徐麗如何結識郭峰並最終決定出走——由內而外破碎的家庭關係,正如這個空空蕩蕩的房間。小說僅在最後一章,以父親李朋為視點,講述一系列事件下的內心軌跡。伴隨時間推移,李朋開始工作並再婚,李一凡出門闖蕩又返回,與徐麗從再會時的冷漠慢慢彌合出不遠不近的關心,而空房間要被拆除,好在家人們終於能達成一種和解的平靜。小說呈現了青年的成長陣痛與父母、生活環境之間的複雜性,情節綿密卻不冗餘,無可奈何中也不失面對生活的希望。
——編 者
因為他曾深夜獨自擊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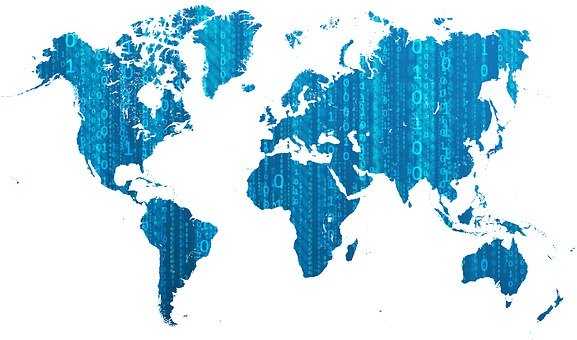
——王棘《空房間》的一種讀法
文|徐晨亮
徐晨亮
一九七九年生於天津,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現任《當代》雜誌副主編。曾任《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
點擊購買
乒乓球拍與深夜擊球
閱讀王棘中篇新作《空房間》的前半程,注意力很容易會在乒乓球拍出現的地方停留片刻。小說一開場,同學們懷疑李一凡偷了球拍,在路上截住他痛毆一番。對於少年李一凡,這樣的疼痛和屈辱就像被劃爛的新衣服,可以挖坑掩藏起來,真正讓他窒息又無法擺脫的是那個叫作「家」的地方:父母靠替人看門房為生,偶爾打打零工,彼此冷若冰霜,總是沒完沒了地吵架。唯一能充當避難所的,便是那個空房間——因寄居的門房過於逼仄,容納不下他和父母以及年幼的弟弟,每晚李一凡都要被送回之前一家人居住的破敗舊樓睡覺。在這裡,他可以無所事事地發呆,或是翻出藏在床與暖氣片之間縫隙里的乒乓球拍,獨自練習顛球或對着牆壁擊球。清脆的「乒乓」響聲伴他度過那些孤獨長夜,可以暫時逃離想要忘記的一切。不過,這樣的時光很快隨着那個夏天一起結束,母親終於無法忍受眼前的生活,拋下父子三個,與異鄉男人私奔。二十年後,快滿三十歲的李一凡因女友懷孕,感到生活突然產生一種新的可能,決定結束艱難的「北漂」生活,回故鄉縣城結婚安家。重新來到舊居,回憶如潮水般將他裹挾,然而,一直到小說結尾,老房子在爆破聲中化為一堆瓦礫,敘事者卻再也沒有提到球拍的去處。
當年李一凡深夜擊球的球拍到哪兒去了?我想,即便留意到球拍在敘事中消失,人們多半也不會這樣發問。因為按照某種近乎常識的說法,「牆上的獵槍是否必須打響」是區分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的重要標誌。在現代小說中,除非作者另有設計,一件小小的道具完成了敘事功能後,自會隱沒於更大的背景,無須再次「打響」。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人們在另外一些場合不會提出類似的問題。事實上,當下有些關於青年寫作特別是「90後」作品的評論,在列舉了三五篇小說的情節之後,便急於對一代人的總體創作傾向提出質疑,貼上沉溺「個人經驗」、迷戀「失敗者形象」的標籤,或將作家筆下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消極心態與退縮行為,與大眾文化領域內「佛系」「喪文化」之類的說法畫上等號。如果循着這樣的思路「按圖索驥」,也可以說《空房間》所寫的小縣城裡瑣碎平庸的生活,大約沒有超出作者的個人經驗;那些灰撲撲的、總像沒睡醒一樣的小人物,很多也可稱為失敗者;他們常常被孤獨感與喪失感所挾持,使得小說情節籠罩着某種無可奈何的情緒……顯然,這樣的讀法僅僅停留於敘事的表層,只關注「球拍」,而忘記了更重要的是人物用「球拍」做過什麼,作者又如何借深夜空房間裡獨自揮拍擊球的場景,顯影那些不可見的內心溫度與情感曲率。
為了找到與《空房間》乃至王棘這一代作家相匹配的讀法,我們應暫時放下某些預定的結論和既有的預期,因為他們的敘事推進常常會讓讀者的期待落空。例如《空房間》裡母親多年後為了兒子的婚事再次與父親會面的場景,顯得如此平淡,並沒有想象中那些戲劇化的互動。若是拿「成長陰影」這樣的慣常視角來分析家庭的離散、母親的出走帶給李一凡的影響,也無助於理解他日後的人生選擇。包括李一凡從北京返回小縣城生活,這樣的情節無疑呼應了時下的社會熱點,但作者沒有濃墨重彩書寫「北漂」青年在「歸去來」過程里的糾結、失落與苦楚,主人公似乎只是順理成章地開啟了另一段生活,甚至有些「若無其事」。人物的「若無其事」,其實也是作者的一種敘事姿態,他並未刻意突顯情節的因果鏈條,而是以李一凡、母親、父親三種視角不斷輪換,讓現在進行時態與回憶、夢境彼此交錯,從而把那些呈現矛盾衝突的節點與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拉到一個敘事平面。就像小說中李一凡突然意識到的,時間是一條無始無終的大河,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漩渦里掙扎。這是王棘希望達致的敘事效果,或許也是激發他開始小說創作的生存體驗。
從「鶴」與「蟬」開始
王棘最早受文壇關注的作品,應是短篇《駕鶴》,曾入選《小說月報》「90後作品小輯」及多種青年作家選本。《駕鶴》與《孩子們套到了兔子》《極樂世界》《明天以後》《火光沖天》《金蟬脫殼》等記錄王棘最初步履的小說,基本都立足於山西鄉村生活實景與他最熟悉的人物。包含處女作《明天以後》在內的好幾篇都寫到鄉村老人,寫老人們被生活「套住」的頹然無力,也寫偶一閃現的對逃離的渴念,他筆下的「鶴」不妨理解為這一渴念的具象化。另外一組寫的則是跟他本人年齡相仿的角色,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金蟬脫殼》,小說里一群在工廠實習的毛頭小伙,困在「無聊無孔不入」的日子裡,發現樹上那些剛剛脫殼的金蟬映射着自己黯淡的未來——被陷阱和羅網重重包圍,想要飛走,卻憂傷地發現翅膀還沒長好。兩組作品的主角看似不同,其實互為鏡像,不管是羽翼未豐還是風燭殘年,同樣身處「蟬」的困境,想象「鶴」的降臨。
在創作談《我們也曾深夜飲酒》中王棘坦言,《金蟬脫殼》的人物原型就是自己和身邊同伴。他本人大學讀工程測量專業,這篇小說就誕生於2014年他在山西南部某小鎮實習期間,工廠里的無聊日常與少年們的內心戲碼,不僅聯結着文本的外部與內部,也與另一組題材相似的文本形成了別有意味的對照——路內小說集《十七歲的輕騎兵》收入的《四十烏鴉鏖戰記》等一系列作品,寫的是1991年冬天到郊外裝配廠實習的四十個學機械維修的技校男生。1973年生的路內與1993年生的王棘相差二十歲,而路內筆下的「烏鴉」們與王棘筆下的「蟬」們,同樣是在空氣凝滯的環境中向着無聊和失敗感做無謂的抵抗,前者如「小野獸」般渾身戾氣,到處惹是生非,後者卻縮在床上抱着手機刷QQ微博、玩遊戲、看小說,中間恰恰也相隔着中國社會激盪變化的二十年。批評家金理曾在《〈十七歲的輕騎兵〉與90年代青年的情感結構》一文中做過精彩分析,「路內和他筆下的這群青年不僅身處社會衝突和斷裂的集結點,而且這段矛盾糾結的歷史直接塑造了小說的內在肌理和文學人物的情感結構」,敘事者「站在歷史無知之幕的門檻上」黯然神傷地回望,「幕外時代的轉型不舍晝夜」,幕內的「烏鴉」們只知道人生劇本早已寫好,卻渾然不知,劇本未來會被時代之手更換,要把落在後面的人甩出軌道的劇烈變動「即將在不遠的地平線上浮現」。在這樣的對照之下,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生活在21世紀10年代的王棘與他筆下的「蟬」們所要面對的歷史處境,他們即將經歷的,都已在父兄輩身上重複過多次,無法擺脫也無法改變,只能提醒自己「生活就是不斷地忍耐」。至少在他們自己看來,命運之流的起點和終點之間,每朵浪花沒有什麼差別,所有的困境都極為相似,不需要戲劇化的情節高潮或敘事的起承轉合去揭示什麼——我想,與其急着對此加以某種價值判斷,不如將之視為被歷史變動所塑造,又與現實經驗相糾纏的一種情感結構,在此基礎上去審視一位年輕小說家如何重新確認小說與生命的意義。
面對所有離開的、消逝的
或許王棘尚未寫出具備足夠說服力、能與前輩相提並論的作品,但他與不少同代寫作者一樣,正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在迷霧中摸索前行,重新打量「陌生卻又似曾相識」的霧中風景,這個過程即便「體會到的是某種挫敗感,但你還得堅信你所做的這一切都是有意義的」(創作談《霧中風景》)。他的「重新打量」也呈現並照亮了那些可見的社會大事件之下,尚未凝固定型、經常被人忽視的經驗。如前文所說,僅僅看到他筆下人物的孤獨、挫敗、傷痛是不夠的,更恰當的解讀,也許要將目光投向那些不可見的、流動的過程:面對孤獨、挫敗、傷痛,人們如何嘗試理解自身處境,不斷找尋免於沉溺的出口。
王棘《離開的消逝的》裡,同樣已有兩個孩子的母親玉枝也曾因異鄉人的到來而幻想「逃離原來的生活」,但與《空房間》不同的是,因對方決意離開,情節滑入了另一個方向。這篇小說里,玉枝關於當年那段無果而終之出軌感情的追憶,被拆解為碎片,重新編織到兒子的「冥婚」儀式、丈夫病重去世等幾段情節之間。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完結與離別如同一次事先的預演,讓她學會從撕裂與失重里擺脫出來,更平靜地面對日後親人的相繼離去,以及正獨自一人走近的生命終點。而《迷失成都之夜》裡,女友再次出走後,男孩曾幻想過,她會跟之前那樣重返身邊,「但隨着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確信這次她不會回來了。我不確定,在南極寒冷的夜裡她是否會想起我?但這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或許,我們終將會互相遺忘」——尚未離開的遲早也必將離開,正在消逝的早已消逝過一次。這是王棘筆下的人物因為一次次「離開」和「消逝」而懂得的事,也是李一凡在空房間裡擊球練習中學會的東西,那些夜晚暗中擊倒他又塑造他,讓他能撐過母親出走後「晦暗至極的時光」,能忍耐作為一隻「蟬」所必須忍耐的一切。
不只李一凡,父親也曾在深夜獨自練習。那次醉酒之後打開電視,體育頻道正在重播一場游泳比賽,他按了靜音,看着運動員們無聲地奮力前游,漸漸有人被甩在後面,「屏幕中只剩下游在最前面的三個人」,而他卻在想着後面的運動員,甚至為他們而傷感,「他心想後面的人一定也知道鮮花和掌聲已經跟他們沒關係了」。看完頒獎式,他久久沒有睡意,便走出家門漫無目的地遊蕩,直到天色變亮。正是在這個和此前此後的夜晚,他發現了自己、前妻、兒子、帶走妻子的異鄉客及身邊人各自困境的相似性,這個發現帶來的不是原諒,而是理解與理解之後的遺忘。
藉由這一幕,大約也更能理解年輕小說家王棘的選擇:選擇寫那些不會出現在屏幕和頒獎式上的人,他們並非失敗者,只是被甩在後面,成為了與鮮花和掌聲無緣的大多數;寫那些半夢半醒、出神恍惚的時刻,他們如何品嘗孤獨、預習離別;寫他們把頭扎在生活的苦水裡,在仰頭離開水面的一瞬大口呼吸。這是他從「鶴與蟬」時期走出後更明確的寫作方向,由此也催生出一種味淡形瘦,疏離於既有閱讀慣性的風格,有時會讓人聯想到理查德·福特等作家關於生活冷酷教誨的書寫,以及為那些倒霉的普通人施放的焰火。同為「90後」作家的甄明哲對此有過精準的形容:那些「最令人壓抑的時刻」「被遮蔽在暗處、推搡到角落的生活」,「被王棘用克制甚至柔和的語言寫下來」,「如果句子有音調的話,他的音調一定比普通人低許多」,「就仿佛土地上沉默許久的一個影子突然開口說話了」。(甄明哲《王棘,黑夜的孩子》)這個影子的低語,也一定會讓我們感受到托卡爾丘克所說的「溫柔」:「溫柔是對另一個存在的深切關注,關注它的脆弱、獨特和對痛苦及時間的無所抵抗。溫柔能捕捉到我們之間的紐帶、相似性和同一性。這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下,世界是鮮活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聯、合作且彼此依存。」(托卡爾丘克獲獎演說《溫柔的講述者》,李怡楠譯,《世界文學》2020年第2期)
點擊購買
空 房 間
文|王棘
作者簡介:
王 棘
一九九三年生,山西靈丘人。作品發表於《中國作家》《上海文學》《作品》等刊,有小說被《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等選載,併入選多個年度選本。現居成都,供職於某雜誌社。
李一凡
李一凡低着頭,順着水流的方向往下遊走去,後來鞋裡進了沙子,他在河邊一塊大石上坐下來,脫掉左腳上的鞋和襪子,抖掉鞋裡的沙礫,把濕了的襪子擰了擰攤在石頭上。一靜下來,他腦中便浮現出在那條巷子裡發生的事情,剛剛壓下去的屈辱感再次冒出了頭。平時他很少走那條窄巷,今天他也不知怎麼突然想要抄近路,其實當時他還沒走進那條巷子,他站在巷口正猶豫時,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們班的宋磊從後面跑到他身邊,是宋磊拉着他的胳膊將他拉進了巷子,說問他件事。他被拉進去後發現另外還有倆人在那裡,宋磊朝他們點了下頭,他發現自己被圍在三人中間。他囁嚅着問宋磊要問他什麼事?球拍的事,宋磊說。宋磊新買的乒乓球拍上周被人偷了。他說不是我拿的。另一個男生使勁推了他一把,他差一點跌倒在地,還沒穩住腳,頭上又挨了一巴掌。宋磊說,你最好乖乖承認,我們都調查清楚了。他不說話。宋磊從他肩膀上搶過他的書包,拉開拉鏈將書包中的所有東西一股腦兒全都倒在地上,並沒有他們要找的球拍。宋磊不甘心,又在書包的側兜里摸了摸,也沒有。他看着宋磊將書包扔在地上,還在上面踩了一腳。宋磊說我知道是你拿的,你把它藏在哪兒了?他不說話。他的背上和腿上挨了幾腳,後來宋磊從兜里掏出一把裁紙刀,他不認識的那倆人一人一條胳膊將他按在牆上,他感到他們扯着他的衣服後擺,接着他便聽到裁紙刀捅破布料的嘶啦聲。
他跳上旁邊的一塊更大的石頭,脫下外套,將衣服背面朝上平攤在石頭表面,這件他穿了不到一個月的防曬服後背上被割了五條超過十厘米長的口子。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念頭是千萬不能讓爸媽看到這件破損的衣服。他在心裡盤算着該如何處理這件衣服,若是他們問起他呢?得編個說得過去的謊,必要時還得再編一個謊話來圓這一個謊。說是忘在學校了,或是姥姥家,都可以,只要當時能糊弄過去就行。
在石頭上平躺下來,把那件防曬服團成一團枕在後腦勺上,他閉上眼,靜靜地聽着流水的聲音,想要將一切全都從腦袋裡清除——乒乓球拍、宋磊、被割破的防曬服、疼痛、爸媽、家,所有這一切。它們漸漸變得模糊,離他越來越遠,仿佛躺在水面上,耳中只剩流水的聲音,偶爾有鳥拍翅膀的撲棱聲,那可能是一隻迅速飛過的喜鵲。他睡着了一會兒。醒來後感覺後背硌得有些痛,他跳下石頭,伸了個懶腰,此時太陽似乎比剛才更熾烈了一些。他三兩下將身上的衣服扒掉堆在石頭上,赤身走進河中。水最深的地方才剛剛沒過他的膝蓋,他在水中躺下,只剩頭露在水面之上,過了一會兒他用手在水底的沙石上支撐着,將頭也沉入水中,他在水裡睜開眼,水面之上的世界顯得一片光亮。他在水中憋氣最多憋一分零幾秒,他一次次將頭浸入水中,又一次次猛地坐起,大口呼吸,直到他厭煩了這遊戲。他從水中出來,又在之前那塊石頭上躺了一會兒,然後才慢慢穿起衣服。臨離開時,他在沙地上挖了一個坑,將那件被割得破爛的防曬服埋了進去。埋好後,他還在上面又踩了幾腳。
門沒鎖,但家裡沒有人。他估計媽可能在旁邊樓上。他們現在住的這間屋子是這個小區的門房,房間朝北是一張木板搭起來的通鋪床,床的對面放着一個立式衣櫃,衣櫃旁邊是一張矮飯櫃,飯櫃頂上放着做飯用的電炒鍋、電飯鍋等鍋碗瓢盆和調料以及他弟弟的玩具球,朝北的窗戶對着大門,朝西的窗戶,正對着小區院子。旁邊二樓三樓是一家旅館,他們搬過來沒倆月,媽就和旅館老闆娘混熟了。現在除了照看門房這邊,她還給旅館打掃衛生,換床單被罩。每次她和爸吵架時她都底氣十足,她說她一個女人做兩份活,他們一家要不是她撐持着,早就喝西北風去了。
塑料積木和玩具挖掘機亂扔在床上,他一個個拿起扔到靠牆的角落。他從飯櫃下面的紙箱裡拿了一袋方便麵,上床靠着被子漫不經心地吃着,他左手在床單上一下一下地拍着,每拍一下,就有一些細小的碎屑塵埃飛向空中,然後在他停頓的間隙又輕飄飄地落下。他用腳趾夾住那個黃色挖掘機,他舉起腿,想象一台真正的機器懸在空中,然後轟然掉了下來,砸在他的腿上,又從腿上滾落下去,他毫髮未損。他聽爸說他以前在工地上幹活時曾開過挖掘機,爸吹噓說他用了一下午時間就摸清了那些門路,爸說如果有人雇用他的話,他會是一個很好的挖掘機司機,說不定慢慢地還可以和其他人合夥或貸款買上一台小一點的挖掘機。當時他和弟弟聽得都很興奮,一臉崇拜地仰頭望着爸,他們以前從來都不知道原來他還開過挖掘機,爸竟然還會開挖掘機。他們要他再多說點關於他是如何開挖掘機的(尤其是弟弟),爸用夾着煙的手指在空中比畫着說,簡單得很,你只需要學會控制那根操作杆就可以了——他的話沒有講完就被媽打斷了,她對爸說,你快閉嘴吧,你要真那麼牛咋現在還天天打零工呢。爸張着嘴似乎想要反駁她,但終究還是沒作聲,轉身端着手機看電子書去了。
下午五點多時,媽從外面回來,她倒了杯水,跨坐在床沿上。他注意到她又燙了頭髮,發尾燙卷了,顏色也由之前的黃色染成了亞麻色。她探身從飯櫃頂上拿過鏡子,一邊照着一邊問他什麼時候回來的,他說早就回來了。她歪過頭看了眼牆上掛着的表,讓他去幼兒園接他弟弟。他下地穿好鞋剛走出去,又聽到她在裡面叫他回去。她從兜里掏出十塊錢,讓他回來的路上順便買些饅頭和豬頭肉。
媽炒了個土豆肉絲,把饅頭熱了熱,爸還沒回來,她說不等他了我們先開吃。弟弟只吃了幾塊豬頭肉便退到後面不吃了,媽也不去管他——要是爸的話一定會哄着他再多吃一些。吃完後,她把碗筷堆在鍋里,往裡舀了一瓢冷水,然後便蓋上了鍋蓋。她坐在床沿聊微信,每次對着手機說完後,她都要點開再聽一遍她剛剛發出去的那句話,他搞不懂她為何如此,而且這使得他很煩躁,好在她沒過多大一會兒便出去了,有人叫她去打麻將。她出去後,家裡立馬清靜了許多,他總算不用再忍受她那不斷重複的話音的折磨了。
晚上快八點時,爸才到家。他看上去有些疲憊,他進家後先坐下來默不作聲地抽了一根煙,然後才在臉盆里洗了手和臉。他打開飯櫃尋找吃的東西,還剩一些豬頭肉,饅頭估計早就涼透了,他將豬頭肉清了,就着吃了兩個冷饅頭。吃完後他也將盤子和筷子放進鍋中。爸問他放假了吧?他說放了。他又點了根煙。過了一會兒,爸坐起來,對着他說,下地穿鞋,我送你上樓上去,早點睡覺吧。
門房的床睡他們一家四口有點擠,每晚他都回他們原先住的那棟樓房去睡,那棟位於城北汽車站旁邊的老樓是他爸媽結婚時買的,離城五里地,一般他都是坐公交去。爸已經將電動車推出來了,他坐上後座,弟弟趴在窗玻璃上對他們揮着手說,拜拜,拜拜。他手搭在爸的肩膀上,電動車啟動,他們出了小區,先向東駛去,然後右拐,朝北行駛,經過政府廣場,廣場上的喧鬧曾一度讓他駐足。一到夜晚,路燈剛亮起,就有一大幫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跳廣場舞,媽也曾來跳過幾次,但她只是湊熱鬧,她還是更愛打麻將。他們從城中穿過,越往北行駛,道路狀況越差,兩邊的建築也越來越參差不齊,既有五六層的老樓房,也有用油氈蓋頂的平房以及院子,他就是在這一片長大的。
爸把車停在樓下,跟他一起上了樓。他們家在六樓,聽人說他們這棟樓建起來有四五十年了,許多原來的住戶都已經搬離這裡。早就有傳言說這裡要拆遷,人們也都盼着拆,但過這麼久了卻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它似乎被遺忘了。
進家後,爸坐在沙發上抽煙,他將書包放在床上,在沙發的另一頭坐下。爸問他考試考得如何,他低下頭,囁嚅着說沒考好。爸嘆了一聲,沒再問他什麼。他鬆了口氣,站起身拿燒水壺去廚房接了水燒上,又挨個把窗台上的花都澆了一遍。爸將煙頭在煙灰缸里摁滅,頭向後仰閉眼靠在沙發上,過了好一會兒,他猛地站起來,說他下去了。
他跑到陽台,趴在窗玻璃上朝外望去,幾分鐘後,他看到爸騎上電動車離開了。他回到客廳,打開電視機,電視裡正播放新聞,家裡的電視有線費已經半年多沒交了,現在就只能收到這一個台,新聞播完後開始放廣告,一個公鴨嗓的男人在推銷一種什麼藥。這人梳着個背頭,頭上和臉上全都油乎乎的,再加上表情浮誇,看着就讓人厭惡。他關掉電視,心想傻子才會聽信他的話買他口中的那個什麼鬼藥。
房間裡空蕩蕩的。他打開電視櫃下層的抽屜,從裡面翻出一個煙盒,還有三根,他抽出一根銜在嘴角,用打火機點燃。他對着鏡子,看着煙霧從自己口中噴出,他抽煙的動作已然像是抽了多年煙的人,最後他將煙頭摁滅在茶几上的煙灰缸中。他倒在床上躺了一會兒,後來突然爬起身,伸手從床與暖氣片之間的縫隙里拿出了那個球拍,它是嶄新的,他撫摸着它,鼻子湊近拍面的膠皮嗅聞,隨之他又想到他那件新買沒多久現在埋在河邊沙地中的防曬衣。他從床頭櫃拿出那顆橙色的乒乓球,他把球拍橫過來,把球放在球拍上,開始顛球,他先是站在原地顛着,後來他在屋子裡來回走動,球始終都能落在拍面上,發出清脆的響聲。他對着牆壁練習擊球,隔壁的住戶去年就已經搬走了,他不用擔心會被敲門。漸漸地,他忘掉了學校、成績單、宋磊以及埋在河邊沙地的防曬服,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顆不斷反彈回來的球上。這天晚上,他在夢中都在打球,不是對着牆壁,而是在一個真正的球檯上和某個人對打,他看不清對面那個人的面容,而且他的眼中只有球,最後他猛地一個反手扣球,他聽到球在地上彈跳時發出的聲響,知道對方沒有接住。
徐 麗
那段時間李朋每天早晨六點不到就起來,飯也不吃,臉也不洗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才回來。這之前李朋已經在家裡閒了一個多月沒有出去幹活了,他們在家隔三岔五就要吵一回。這次他跟他的幾個朋友去幾十里外的山上刨樹坑,說是按數量計算工錢,多勞多得,平均下來一天能賺三四百塊。徐麗說不管他能賺多少回來,只要他不整天在家躺着就行,不然她看着他總覺得礙眼,控制不住生氣。
倆孩子前幾天回村里李朋爸媽家了。那天徐麗在門口飯館吃了早飯,回去時看到一個男人正在門房那裡張望,他的身邊立着一個銀色的拉杆箱。徐麗過去問他是要住旅館?男人回答說是,他扶了下眼鏡,說他在外面看到旅館的招牌,但不知從哪裡上去。徐麗指着樓梯口的方位說,旅館在樓上,我帶你去。她問他是從外地來的吧?他說是,他問她是旅館老闆?徐麗回頭笑說不是,我就是個打工的。他低聲說了聲哦。
老闆娘不在,徐麗拿出她的那把鑰匙開了門,在那張桌子前坐下,從抽屜里找出登記簿,問男人要了他的身份證,在登記簿上抄寫他的身份信息,他的名字叫郭峰,一九七八年生,身份證照片上的他沒戴眼鏡。她問他打算住多長時間,他回答說一個禮拜左右,不過也說不準,可能提前離開也可能要待更久。他的普通話很標準,聽不出有某個地方的口音。登記好後,徐麗問男人要了一百的押金,給了他一把鑰匙,帶他去了他住的房間。離開時她對他說要是退房時老闆娘不在,就去樓下小區的門房找她。
天黑時,徐麗正準備出去吃飯,她推開門,看到下午那個男人站在門外,她想起了他的名字——郭峰。她問他有事嗎?他說他想問一下附近有沒有什麼比較好吃的飯館。徐麗說對面那家粗糧館就不錯。他對她說了聲謝謝,又問徐麗也要出去吃飯嗎?徐麗說是,他便說他跟她一起。徐麗說她要去吃麵,他說那他也吃麵。他們來到麵館,徐麗點了小碗加豆腐乾,郭峰點了大碗加雞蛋,又點了兩個涼菜,要了三瓶啤酒。
確認徐麗不喝啤酒後,他便獨自喝了起來。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天,徐麗從他口中得知他老家是河北的,現在是某化妝品品牌的業務經理,他來她們這裡主要是為了推廣該化妝品品牌。徐麗問他怎麼不去大城市,反而來這個沒多少人的小縣城?他解釋說大城市也去了不少,小縣城也不能不去,而且同樣重要。他說得雲裡霧裡的,大部分內容徐麗都聽不太懂。後來等他喝完那三瓶啤酒他們一起回去,門房的燈黑着,李朋還沒回來,郭峰問她就她一人?她說孩子回爺爺奶奶家去了。他對她說早點休息。徐麗說你也早點休息。
電視開着,可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電視節目上,她只是需要它發出一些聲音。她拿起織了一半的毛衣打了幾針,過了一會兒發現針法全錯了,只好又一一拆掉。李朋晚上九點多時才回來,他灰頭土臉地走到屋裡,鞋也不脫便倒在床上。她放下手裡的東西,推着他讓他起來到院子裡拍一下身上的土。她讓他上樓去旅館沒人住的房間裡沖一下,他說他太累了,任她說什麼也不去,她說不動他,只好給他倒了一盆水,讓他洗頭髮。夜裡李朋發出的鼾聲持續地在徐麗耳邊折磨着她,再加上天熱,她根本無法入眠。她坐起來套上褲子,披了件衣服,來到院子裡,她抬頭往上望,天上掛着一彎下弦月,二樓最裡面的那個房間燈還亮着,窗簾已經拉上,那個男人是不是睡着忘記關燈了?徐麗還記得他喝了三瓶啤酒,應該不會失眠了吧?
第二天傍晚時分郭峰從外面回來,他在門房窗前站住,窗戶沒關,趴窗框上問徐麗,要不要一起去吃飯?我請你。她沒反應過來,正猶豫間,他已當她同意了,他朝樓梯那裡走去,邊走邊說,你等我一下,我先上去換件衣服。幾分鐘後他下來了,換了一件亞麻短袖襯衫,頭髮明顯也重新梳理過。這一次她喝了兩杯他給她倒的啤酒,他要倒第三杯時她把杯子用手掌罩住了,他笑着說他看得出她還能喝,不過他並沒有再勸她。他給她講他幾年前在南方城市的經歷,她聽得很入迷。她從沒去過南方,她最遠只去過一次北京,她對北京的印象不是很好,那時她在服裝店賣衣服,住的是地下室,吃得也不好,每天要看顧客的臉色就不說了,還經常挨老闆的罵,她沒做滿三個月就跟老闆娘吵了一架,跑回來了。然後她就結了婚,結婚的對象雖是她自己挑的,她仍常常感覺自己被拴住了,被她的老公、孩子以及他們共同組成的那個家。
李朋在家休息了三天,這幾天時間她沒看到郭峰,她偶爾想起他,猜測他或許已經離開她們縣城去其他地方了。她看不慣李朋整天躺在那裡看電子書,他從來不想想如何多賺點錢,一天到晚得過且過,她控制不住自己尋着由頭和他吵架,奇怪的是每次吵完後,她都會感覺要更輕鬆一些,過一會兒她又會覺得沒意思,沒勁。她看得出他一定也有這樣的感覺,她估計身邊許多人可能也都有此感受,她知道大部分人都是這樣過完一輩子的。
那天徐麗在美髮店碰到了一凡的班主任劉虹。那是一個小個子女人,戴一副黑框眼鏡,最明顯的特徵是兩顆突出的門牙。徐麗專門等了劉老師一會兒,她們一起從理髮店出來,她對劉老師說了些感謝的話,希望老師以後多多敦促一凡學習。劉老師只點了點頭,快分別時,劉老師站住對徐麗說放假前班裡一個同學丟了一副球拍,私下裡有些同學說是一凡拿了。她意味深長地看了徐麗一眼,沒再說其他的。徐麗臉一下紅了,她問有人看到是一凡拿的了?劉老師說,沒有,只是一些學生私下在說,也不一定是真的,不過你回去最好也問一下一凡。徐麗說好,我回去問問他,給老師添麻煩了。
去年一凡曾偷過別的同學的鋼筆,老師查了出來,她被叫去了學校。她還記得那時的那種恥辱感,回到家後她讓李朋狠狠教訓了那孩子一頓,並讓他保證以後不會再拿別人的東西。今年他升了初中,她以為他長大了、懂事了,沒想到他還是沒能改掉那個壞毛病。晚上李朋回來後她跟他講了劉老師說的那件事,李朋聽後嘆了一聲說,等他回來了再問問他,看看他承不承認。「要是真的,這次我扒了他的皮,我就不信他不改。」隨後他們陷入沉默之中,那孩子不在眼前,他們心中的氣都沒地方撒。
…選讀完…
(文中部分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責任編輯】:趙依
【視覺設計】:李楊
點擊購買
讀《中國作家》
品文學中國
訂閱全年 限時優惠
1
國內郵發代號
《中國作家·文學》 2-545
2
廣告發行出版電話
010-64272713
3
發行部郵箱
zgzjfxb@zgzjzzs.com
4
本刊網址
www.zgzjzz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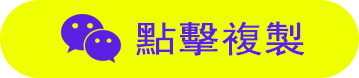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有情感誤區能找情感機構有專業的老師指導,心情也好多了
求助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