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雲也退
摘編 | 董牧孜
阿凡達,或加繆的「生長的石頭」
那些年,有一種奮戰的氣氛在這個社會裡到處滋生。巨大的國際任務迫使我們時刻地聽到這樣的宣告:我們剛入狀態,我們正當年。奧運會把人群往北京引過去,世界博覽會又把人群拖到了上海,在兩者之間,我也破天荒地,把一部電影在影院裡連看三遍。真稀罕,大概一輩子就這一回,而且看的時候心無旁騖,沒上廁所,也沒有動手裡的零食。

這是《阿凡達》,當那些絢麗的鳥兒起飛,我感到,仿佛是當年那個樸素無華的尼爾斯升級了裝備。我們的視野早已突破了1900年,拉格洛夫眼中瑞典田野的邊界,也突破了1900年被康拉德矚目的、遭到白人殖民者遠程控制的南美的疆域。我們在想象古老的祖先,外太空生命,和不為人知的異域的景象。雖然「史詩巨片」 仍不脫那些套路,比如最大的反角在白熱化的格鬥中,最後一刻倒地,正義的一方迎來無力慶祝的慘勝,又比如日久生情的「愛上敵人」,但我越來越心無旁騖,越來越愛看的一個場景,是阿凡達人圍聚在生命之樹前搖擺左右平伸的臂膀,從喉嚨深處吐出長嘯如利劍。
《尼爾斯騎鵝旅行記》刻畫了一個不愛學習、喜歡惡作劇的頑皮小男孩尼爾斯歷險的故事。
那不單單是一種原始信仰的呈現(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信仰缺失要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崩潰負責),讓我沉浸的,是那種詩意的團結感,溫暖人心的共在感。傑克帶着使命來此,他是「異己」,徒有「我族」外表的「非我族類」,而在他尋求融入潘多拉社會時,他那帶有傲慢色彩的使命感就被消解了。原始壓過了文明。
這裡的「原始文化」當然被大大美化過,絢麗,純淨,和諧,如果有部落之間的野蠻攻伐,那恐怕要到續作中才會展開。可我仍然喜歡這種容納異己的過程,因為在日常中,我感覺不到任何共同體的存在,我早就養成了卡內蒂式的旁觀者的性格,可如今《阿凡達》卻在鼓動我去參與,它讓我想起一篇小說:阿爾貝·加繆的《生長的石頭》。
你看!有一天,一尊耶穌雕塑從海上逆着河水來到這裡。漁民們發現了它。真美呀!真美!於是,他們把它洗乾淨放進山洞。現在,山洞裡長了一塊石頭。每年,大家都來慶祝。你拿着錘子,砸呀,砸呀,為了得到祝福。你猜怎麼着,石頭老是長,你老是砸。真是奇蹟。
達拉斯特,一位水利工程師,從第一世界法國來到第三世界南美的一個村莊,正遇當地人的主耶穌節,接待者向他介紹這塊神奇的石頭。「生長的石頭」成了小說的核心隱喻,它就像阿凡達人的生命之樹,人們可以通過向它祈福來獲得內心的平靜和安全感,甚至相信會有奇蹟發生。加繆不是基督徒,他寫耶穌節,不過是為了為此後的情節埋下伏線:達拉斯特領悟到了這種部落文化的向心力,他情不自禁地想融入它。這種嚮往,同他被派駐到這裡來扶修水利設施的剛性使命無關,是一種額外收穫。
《勇敢的人死於傷心》,雲也退著,理想國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月版
薩特過於強大,加繆與他不同
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就是看看小說,再看看自己。不過有時,文學會用一種哲學來暗暗侵入自己,比如存在主義。在我最需要光的時候,存在主義文學給了我光,用常常近乎陰暗的方式。它的奧義就在薩特和加繆兩句最有名的話里:他人即地獄,所以獨自推石頭的西緒福斯是幸福的。中國人的哲學教你怎麼圓融處世,西人的存在主義卻說,一個人待着,最好。
薩特
薩特是一個過於強大的作家,強大且偉大。我讀他在解放後的巴黎寫的隨筆,驚呆了,世相聽命於他,服從他的旁觀、洞察和冷不丁的吶喊,但又不會讓人覺得他在曲解事實,故意誤導讀者。我讀紀德高歌母親之死時的感覺也是驚呆的,可薩特在《文字生涯》裡,講到自己的母親如何生下自己時的那種六親不認的勁頭,又給震驚添上了新的理由:
......讓—巴蒂斯特早想進海軍軍官學校,為的是要看大海。他當上海軍軍官後,在交趾支那得了瘧疾,病得力竭體衰。1904 年他在瑟堡結識了安娜-瑪麗·施韋澤, 征服了這個沒有人要的高個兒姑娘,娶她為妻,並飛快地讓她生下一個孩子,這就是我。從此他便想到死神那裡求一個棲身之地。
我們心裡碰不得的東西,薩特拎個保齡球進來,隨隨便便全給碰翻了。連母親都可以是局外人,厲害,那麼說出「今天,媽媽死了」的加繆應當更不用說了。薩特在闡釋《局外人》的時候,特地強調「我自己對我自己而言也是局外人」,「某些時候在鏡子裡朝我們走來的陌生人」,而偏是這樣徹底冷感的人還不會自殺,還樂於周而復始地推石頭,活下去。這真的太厲害。
可當年讀了《生長的石頭》,我才知道他倆不一樣。原來石頭不僅有被西緒福斯推着上山一種用途,加繆的思想,也絕不是「存在主義」「荒謬」幾個標籤可以涵蓋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叫《阿爾及爾之夏》,富含哲學的優美和堅實,在其中,加繆多次提到地中海邊的石頭,它們白天吸收夏日的餘熱,在夜裡釋放出來,給恐怕受涼的草木披一層晚裝。踩在石頭上,加繆一躍入海,他說,這裡的人們不說「去游泳」,而說「去溺泳」,那意思海水要沒頂,把人從頭到腳、徹徹底底地汆一汆。
他固然讚美天地間孤獨的個體,卻也曾歌唱一種風俗的開化:
人們在海港里游泳,在救生圈上休息。任何人如果游經一個浮圈,發覺上面漂着一個日光浴的美人,便會對它的同伴們大叫:「告訴你們,這是只海鷗! 」這些都是健康的玩笑。它們顯然構成了這些年輕人的理想......但他們只是單純地「在陽光中舒暢」。在這時代,這種習俗實在是再重要不過了。兩千年來第一次,肉體赤裸裸地出現在海灘上。
此時的他像帕斯捷爾納克一樣,為人類奔放不羈的多樣性而激動。身高一米五二的薩特很難在乎這些,而儀容酷肖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的加繆則不然,對他來說,那種冷冷的局外人意識,是兒時以來的切身體驗,卻也是生命額外的賜予。局外人通常意味着挑剔,但加繆很樂於回答這些問題:家是什麼,愛是什麼,祖國是什麼。1950年,他在一則日記里寫了句話:「從在每個人身上尋找正確的東西開始。」
這真是授人以漁。達拉斯特就是這麼實踐的:伊瓜貝小鎮的官員對他重禮相迎,可他不想躺在賓館裡足吃足喝,而渴望接觸那些不怎麼敢接近他的、圍着纏腰布的黑人 ( 監工坦然相告:「他們是最窮的」 ),那些虔誠敬神的普通人。同樣的,《阿凡達》中的傑克雖然對陌生之地不無疑慮,也看到猛獸們面目可怖,卻也認出他們對別的地盤上的主人的尊重,兇悍的伊卡蘭,不也能與人生死為伴?
道德關係因而建立了起來——不但求真,而且「求正」。
把從文學中領受的東西,放回到現實之中
2009年的時候,地鐵已經很發達。像電梯一樣,你按向上的箭頭,就知道它不可能往下走,走進地鐵,你也明白它一定能按時幫你抵達目的地。工具處在人的馴服之下,分毫不爽地為人服務,我很小的時候體驗過的,擁擠的公交車裡一隻只手接力傳遞車票的惡劣感覺終於一去不返。然而,人仍是不可測的,不管是在車廂里還是在地鐵上,舉目所見,他者都是異己。
在地鐵里,我被一個穿着鼓鼓囊囊的外套的胖男人堵着通往出口的路,內心就生出了躁鬱。「能讓一下嗎?」我說,語氣中帶出一種責備。那個男人轉下身子讓開了。「慢點」,他說。
我離開地鐵很久,還記着他說的這兩個字:「慢點。」
在別人身上看到「正」,或許本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不必像加繆那樣,押上一個有着陽光大海、少男少女的環境,才會想到「活着真好,生活中處處有美」。不過,隆重一些的投入常常也是必需的,就好比發現了一顆太陽系行星,增加了一條人所共知的天文常識,之前卻耗掉了很多代人類的精力。加繆必須把他的認識連同產生這種認識的外因一併交出去,我一遍遍讀他寫的北非,越來越覺得,他之迫切求「正」,是因為他渴望讓自己度過的一切都擁有意義。
他說,阿爾及爾的電影院裡出售一種菱形薄荷糖,糖紙上常常貼着紅色的標籤,上面寫着「一切能喚起人們愛情的話語」,比如這樣的問答:「問君何時帶我入洞房? 」 「明年春天。」 「您愛我嗎?」 「瘋狂地。」
他曾說,巴勒固的青年都很早就結婚成家,一生的精力在年輕時就耗竭,「一個三十歲的工人已經發盡了他手中的牌。他處在老婆和孩子之間,等待着終年」。但意義在於,一個人可以了解這個過程,這個先獲得恩賜、然後被剝奪的過程,恩賜來得突然,來得確切,來得慷慨,去的時候則是一場毫無情義的「焚盡」。
他曾說,阿爾及爾的殯儀館老闆喜歡開一種玩笑:他們駕着靈車在路上碰到漂亮妞時,會喊道:「要搭車嗎,小妹? 」看上去很不吉利 ,但人們在聽到一個凶 耗 時也會褻瀆不敬地講這樣的話:「可憐的傢伙,他再也不會唱歌了」,或像一個奧蘭女人那樣說自己從未愛過的死去的丈夫:「上帝把他賜予我,又把他從我身邊帶走。」 意義在於看到其中的暗示:就在一個邀人生存的國度里,死亡因其無處不在而缺乏神聖氣氛。「尤其就在這墓地的牆垣下,」他補充道,「貝勒固的青年們幽會着,女孩們讓人親吻着、愛撫着。」
他真的比薩特更敏感,需求的更多,也更容易受傷害。1945年法國解放後,人們抓出「法奸」,把男人絞死,把女人剃頭,加繆本是根正苗紅的反法西斯戰士,卻看不下去了,即使對貨真價實的法奸——通敵記者羅貝爾·布拉西雅克(Robert Brasillach),加繆也參加了上書情願,要求對他網開一面。這段故事很有名,但對照加繆的另一篇故鄉散文《運動》來理解,能得到更多的啟發:
前途無量的青年們,或新手們,參加拳賽只不過是為了尋樂。為了急於證明這點,他們一開始便屠殺對方,完全不顧拳擊技巧。他們從來沒有撐過三回合的。當晚的英雄是年輕的「毛頭飛機」,他平常在餐館的陽台上買彩券。 當然,他的對手在第二回合開始時,嘗到一個像螺旋槳的拳頭後,便尷尬地衝出擂台。
群眾變得非常激動,但這仍然是一種禮貌的行為。在神聖的氣氛中,他們呼吸着沉濁的皮膚油膏味。他們注視着這一連串緩慢的祭典和毫無節制的犧牲,影射在白牆上打鬥者的和解態勢,使得這些祭典和犧牲顯得更逼真。這些都是野蠻宗教的開場白。昏迷後來才會登場。
拳擊是野蠻的遊戲,對賽雙方往往來自奧蘭和阿爾及爾這兩座一貫互相看不起的北非城市,所以一場比賽有着相當的象徵意義。有人在流血,有觀眾在惡毒地叫喊 「打他的襠!」 後來,軍警不得不進場把那些搬起椅子準備打架的人分開,可加繆斟酌着字詞,說這是「善良人的憤怒」。他又說,一旦新一場比賽開始,人們就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回到原位; 而當一名法國拳手登台,所有觀眾便一股腦地支持起了他的阿爾及利亞對手,不管他來自奧蘭還是阿爾及爾。
野蠻的畫面,流血的畫面,經過他的記憶和文字的重塑後依然野蠻而流血,卻帶上了意義,僅僅是為了這些,他都無法接受眼前的爭鬥。「肅奸」運動中的憤怒,缺少制衡的力量,更缺少本真,而是夾帶着各種自私的欲望。他所來自的那個陽光充沛的地中海世界裡,並不是沒有你死我活這一條的,但他能從那裡看到「正」的質素,而在眼前的政治大潮中,他看不到。
我的問題,是要把從文學中領受的東西放回到現實之中。這真不容易。誰知道,即便我能乘坐時光機器回到加繆的北非,是否也會發現那裡的不盡人意呢? 殯儀館老闆一點都不可愛,在墓地里擁吻的人們,或許有幾分猥瑣,而拳台上下的人們,他們廝打和辱罵的動靜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
有個老太太,常常造訪一間烘焙房。「我又來了,」她說,「我要買一個不太甜的麵包。」她的駝背很顯眼,點評所有麵包的熱情很執着,她指着玻璃櫃裡的一樣樣東西,嘀咕好半天,這個模樣不好,那個一看就發酵不當,還有這個,「你們的水平比以前高一些了,我上次來買還不是這種色澤......」
「貴是貴的,我給你二十五塊,我願意」,她摸着錢,仍然買了之前多次買過的那個品種,「貴是貴的......」我一次次看到她,努力想象自己是個孩子,但有好奇,不會輕易地露出嫌棄。人,人就是如此,我也會有這一天,也許跟她聊聊,我會發現這是一個性情有趣的人,有過不同尋常的早年,那時的她擁有過別人不敢奢望的選擇,而她執着地守着往日的任性,至死方休。這沒什麼可嫌棄的,這也是有關「正」的。
不讀小說,我永遠不會這麼看人。他人與我何干,如果他們不能帶來我需要的東西? 加繆寫《鼠疫》,裡面有個臥床不起的氣喘老頭,每天把鷹嘴豆在兩個鍋子裡數來數去,關心着霍亂是不是正在流行,讓了無生氣的城市發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他是個面孔鐵板、滿是皺紋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兩滿鍋鷹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來坐在床上,醫生進來時,他把身子往後一仰,想喘口氣,重又發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聲哮嗚。
「怎麼啦,醫生,」他說,「是霍亂嗎?」
在《鼠疫》裡,陽光燦爛的故鄉變得黯淡,石頭回歸毫無生氣的本來面目,沙灘上的年輕人消失了,醫院和老病之人的存在感浮現。里厄醫生、塔魯、朗貝爾,幾位主角都在掙扎,履行或者逃避職責,並思考行動的意義,死亡的意義——唯有大海依然是人回退的去處。2013年,在加繆百年誕辰的時候,企鵝出版社重新給他的代表作出了一套新版本,其中《鼠疫》的封面就是海,白色的浪紋細密如織,層層向遠方推進。
2013年出版的《鼠疫》,企鵝出版社
因為加繆的緣故,我覺得自己離人近了一點。
人可以僅憑其原樣而獲得不無感情的注意,就像加繆在《鼠疫》中,及在諸多故鄉散文中所做的那樣。薩特褫奪了我對任何人多餘的敬意,他幹得漂亮,他人是地獄,本質上不可溝通,會惹出無盡的麻煩——這千真萬確,但是,加繆在評論《蒂博一家》的時候說的一句話同樣引起我的認同:「事實上,和他人在一起而同時保持正確是不可能的……唯一真實的進步,在於認識到自己始終在犯錯。」
都無法有一說一地解釋這樣的句子。我必須讀,讀,讀,從《局 外人》《鼠疫》《墮落》《阿爾及爾之夏》《正義者》一路讀到《第一個人》,才能明白加繆要說的是什麼,他講的「正」「正確」是從他的世界裡自然孕生出來的東西,外人憑着自帶的「前知識」去理解,就會解釋得很俗很低檔。他那部未完遺作《第一個人》,依然從他的北非童年,從「人之初」寫起,本就想定名為《亞當》,在其中,他再一次重述個人的記憶和感受,決不美化,而是元氣淋漓地寫盡失落、挫敗、哀傷、孤獨。在小說中斷的地方,加繆的詞句又讓我想起了紀德,讓青春的消逝成為一場慶典:
生活在這塊沒有祖先,也沒有回憶的土地上,在他之前的人都已經逝去,而且更為徹底,在這塊土地上,衰老無法找到任何方法可以治癒它……他今天終於體會到生活、青春、生命從身邊溜走,這一切他絲毫無法挽留,只有放棄它們,在盲目的期待之中,這麼多年來,這種隱約的力量一直支撐他度日,永不枯竭……
一個階段剛好結束,而下一個階段尚未開始:接下去,主角就要開始尋父了。加繆會如何架構,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什麼繆斯神附了體,連死都仿佛是精美切割的一刀?1960年1月4日,他乘坐的那輛 Facel-Vega HK500 以比地鐵還快的車速撞上了兩棵大樹,死的時候,包里裝着《第一個人》手稿,以及一份《奧賽羅》的譯稿和一個尼采的譯本。或許要歸功於整理者,殘缺的《第一個人》讀來仿佛有意安排的殘缺,就像斷臂的維納斯, 就像寫不完的《城堡》,正因其寫不完,它才成為《城堡》。
他未必討厭孤獨
可文學依然是文學。誠實地講,我還是只能從《阿凡達》或《生長的石頭》裡去體會「融入」的美好。我面前有一道鴻溝,從早年旁觀成人時起就開始形成,並逐漸擴大。主動去融入,對我是一種很高的要求,正如同我希望我所住的地方,就連乞丐也能吹拉彈唱, 衣着儘量體面一點,而不要坐在一個骯髒的平板車上,用兩條殘肢往前滑行。老人可以有趣,但不可以醜陋,孩子們最好不要太拿自己當祖國花朵。
可是加繆所說的「祖國」,於他自己而言,也是不可企及的。寫作《生長的石頭》,正是他情緒消沉的時候,那是20世紀50年代,他的故鄉,他用來抵抗法國政治現實的、為他源源不斷地提供意義的北非,其局勢恰恰是不讓他「融入」的:宗主國法國的白人,和殖民地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而加繆生在殖民地,人卻是法國籍,於是發現自己被夾在中間,不受任何一方的信任。於是,他像《約拿》中所寫的,只好去做一個「工作中的藝術家」,通過寫小說來抵抗一個沒有許諾的未來。
阿爾貝·加繆 (Albert Camus,1913—1960)
他未必討厭孤獨,沒有孤獨,哪來這許多的文字生產呢?《重返蒂巴薩》是篇我第一次讀就哭出聲的文章,後來又哭了好多次:當人們一旦有機會強烈地愛過,就將畢生去追尋那種熱情和那種光明。放棄美,放棄與美相連的官能幸福,專一地為不幸效勞,這要求一種我所缺乏的崇高。但是,無論如何,任何強迫人們排斥一方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孤立的美最後要變成丑,孤獨的正義最後要變成壓迫。誰想為一方效勞而排斥另一方,就將不為任何人效勞,也不為自己效勞,最終將雙倍地為不義效勞。有朝一日,由於過分地僵硬,將不再有什麼東西引起人們的讚嘆,一切都不足為奇,生活就要重新開始。那將是流放的時代,生命乾枯的時代,靈魂死滅的時代。為了再生,必須有一種恩惠、忘我和一個祖國……
真的,21世紀的頭十年,讀加繆是一種足可讓我炫富的修行。他用文字喚出的祖國,太真實,太可觸了:那就是小說里的達拉斯特扛起基督遺骸,替一個陌生人走完還願之路的樣子,那就是電影裡土著人端坐地上,在有靈魂的草木之間舞蹈的樣子。我總在獨自一人為這些打破藩籬、容納他人的故事感動不已,覺得抵達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洞裡的石頭無聲地長,砸掉一點,長出一點,不縮小,也不囂張地要掙破洞穴的束縛。《阿凡達》那會兒,人們都在說信仰,我覺得,如果必須得有信仰,那麼就要信如這麼一塊石頭一樣的信仰,說它是古希臘的溫良公允也行,說是夏日地中海的和平博大也行,總之,一個這樣的神,得能讓素不相識的人成為兄弟姐妹。加繆當真這麼公允而博大地實踐了。他曾說薩特是一個「價值的暴君」,一個極端分子,硬要「為一方效勞而排斥另一方」。然而,就在兩人的矛盾徹底爆發後不久,加繆卻又這樣寫:「每一個對手都是內心的聲音之一,它說:我們不妨沉默吧;我們必須傾聽這種聲音,為了糾正、適應或重申我們得以一瞥的屈指可數的真理。」
簡直完美,雖然也只是死後的完美,雖然這種剛勁緊湊的道德感通常只招引葉公好龍之人。如今,他的照片恐怕是有史以來所有作家中所見最多的,偶像派的地位牢不可破,我也終於得以放下仰望的姿態,平視一個事實:他也曾像瑞士人馬克斯·弗里施那樣,用文學為盾,來替自己的私德貳行擋箭。
1954年,他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 Camus)險些自殺,傳記作家說,那是因為加繆屢屢跟別的女人上床,把她搞得十分絕望——這種事似乎很難用特殊的童年、肺結核、獨特的戲劇人格或者俊朗的外形來辯護。於是後來,加繆寫了《墮落》,其主人公克拉芒斯集中了多個人物的形象,包括他自己,克拉芒斯坐在阿姆斯特丹圈形的運河之中,猶如置身《神曲》中的地獄,當他承認,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無法不回頭時,加繆便在懺悔,或者說,開脫自己的罪過。
但他做過的一切都可以為他加分,融入他的傳奇。這種融入如同絲綢跌落一般的順遂:如果緋聞能凸現一個人蓬勃的生命力,而這個人恰恰又是加繆,又有何不可呢?他無法不惹人陶醉:他對生命之荒謬可悲的認知是真誠的,他對男歡女愛、碧海藍天的享受與歌頌,也是真誠的。無論是寫下最消極、最沉痛的言語,還是表達豪情壯志,他都給人留下同等的好感。
想要英雄主義很容易,快樂卻很難
就連那輛死亡之車也帶上了傳奇色彩。加繆是不喜歡汽車的,他曾說,自己一輩子都討厭遠途自駕,尤其害怕開快車。然而這個總是尋花問柳的男人,總是令人同情的不忠的丈夫,卻坐上了那輛 Facel-V ega HK500,一款以速度快著稱,又曾被暢銷色情小說家傑姬·柯林斯(Jackie Collins)形容為坐進去後 「就跟做一次好爽的愛一樣,你盼着高潮的一刻一直持續下去……」 的豪車。開車的人是他出版社的闊朋友,馬塞爾·伽利馬,車上還有一條狗,車禍發生後,據說最先趕到現場的當地醫生,名字叫馬塞爾·加繆。
真是一位「荒誕王子」。不管這些逸聞有多少來自後人的虛構,人們期望他獲得「幸福之死」——這也是他的一部戲劇的名字——的意願是蒼天可鑑的。
我有一個感覺,任何人想要為自己的行為物色辯護士,都可以找上加繆。他是個有求必應的神,從他那裡,任何人可以得到自己的所需 : 他證明了孤獨有多美好,也呼籲團結值得追求;他鼓勵人放眼天地萬物,也支持你去享受肌膚之親。無論是西緒福斯的隱喻,還是《反抗者》中對革命幻象的批評,都可讓人或安於現狀,或設法改變;你若想做一個及時行樂的人,那麼加繆是一份能讓你欣喜 若狂的思想資源,他就是一個崇尚肉慾的人,認為感官悉出自天然,可以填補在一個貧窮、無知、沉默的家庭里的空虛感;你也大可宣稱自己像加繆一樣,早就看透了世界的無意義,所以才按照他的話去實踐:「想要英雄主義很容易,」他說,「快樂卻很難。」
光是為他挑墓志銘,就可以挑花眼。仿佛每一天,加繆都在留下讓人銘記自己的句子。他的死,和《局外人》中莫爾索的死,幾乎是重合的,也必須重合,他的遺言必須重合於莫爾索的心聲,那種對無意義的死亡之意義的強悍宣告:
面對着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第一次,如此,曾經幸福,仍然幸福。薩特的修辭術是對抗加繆的修辭術的,他準確地說過,加繆的自我道德高標,是一種「判處自己去判別人刑」的行為。只是對我而言,他「判」給我的刑,就是幸福。但這刑也同樣是薩特給我的。存在主義在我頭腦中加設了一個「世界」的概念,遇到困境的時候,我會覺得這是與世界的 矛盾,與起源、與「人之初」的矛盾,心裡就會明白,這是我降臨此世的結果之一。唯有如此,才能不一味轉向他人,才能不計算得失,才能放下自己。放下,也許我永遠入不了人海,但我可以放下。
本文節選自雲也退的隨筆集《勇敢的人死於傷心:與文學為伴的生活冒險》之《被判幸福》,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由理想國授權發布。
作者丨雲也退
摘編丨董牧孜
編輯丨張進
校對丨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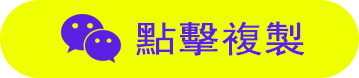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一閨蜜諮詢過,很專業也很靠譜,是一家權威諮詢機構
如果發信息,對方就是不回復,還不刪微信怎麼挽回?
求助